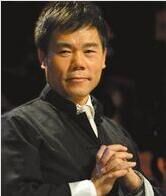【摘要】: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邏輯批判進行修補的重要任務是,重新構建新型的勞動合作模式,提升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化”維度,降低乃至逐漸削弱資本生產力的任務。這一課題的深化,不僅會在理論上刷新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解放理念的認識,同時也將使中國道路為人類新型文明所做的探索提供智力支撐。
報紙原文:《對資本邏輯批判進行修補》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孫亮
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敘述方式中,資本邏輯批判無疑是標識馬克思思想深度最為重要的闡釋視角。依據這些闡釋者們的文本,我們可以輕易地看到資本作為“關系”對現代社會中人的存在方式與存在觀念的建構力度。無須我們去援引沃林·懷特曾在《展望真實烏托邦》中以資本邏輯的罪名列舉了資本主義之所以壞的“十一條論綱”,又或哈維等一批耕耘在《資本論》這塊思想沃土之上的斗士,只需要我們看看當下漢語學術界的文本,便可以知曉資本邏輯批判與歷史唯物主義之間的“吻合度”。在如此流行的觀念面前,我試圖拋出自己的不成熟的一點質疑,指明上述的吻合其實是存在偏差的,對這種偏差的警惕便是新的生存方式開啟可能性的地平線。
資本邏輯批判是封閉的圍城
如果我們從資本邏輯批判的視角來進行現代社會的解讀,我們會將資本看作是對整個社會的“同一化”的力量,猶如一個吸納整個世界的魔法瓶,資本突破了一個又一個界限,完成了一個又一個抽象世界的建構。用《資本論》中馬克思最喜歡的詞“表現為”來講,這個世界的人們丟棄了真實,而投入到了“表現為”的“景觀世界”的懷抱之中。馬克思曾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意欲告知人們,我們遺忘了“財富一般”,僅僅將目光盯著“財富特殊”,即資本主義的財富形式——商品世界。身處于這樣的世界,人的整個理性思維早已被資本收編了,交換的價值法則成為生活的唯一準則,資本邏輯的力度在此便被凸顯出來。
但是,如何打破資本邏輯呢?則又至少呈現為下述兩種方案:一是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思路中,這當然是一種人們早已熟知的資本外部革命的方式,依據這種方式,交換增值的邏輯被消除掉,生產資料私有轉變為公有,等等;二是借助資本自否定的辯證法,推論出資本邏輯瓦解的必然性。由此,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下的出場便是用資本邏輯視角分析各種社會問題:生態的、價值的等。兩種解決方案無疑則要么是激進的、要么是無限期的等待。
那么,對于個人來講,這樣的闡釋方案是外在的,它似乎是一套僅僅停留在文本之中的話語。每個人越是感覺外在資本邏輯的強大,越是無力地去改變,這個世界已經牢固地生成為我們的存在的“圍城”,將我們困在其中了。資本邏輯的闡釋采用了同一性的邏輯,卻從來不去努力揭示資本邏輯在同一性過程中的“剩余”,即那些不能同一之“關系”,諸如愛、情感、生活本身的豐富性與意義。當然,在奈格里等人那里,這些作為生命政治勞動也可能被資本突破,但是,至少這種非同一性是存在的,而且也正是人類突破資本時代的一種可能,這理應成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向度。在這個意義上講,資本邏輯批判暗含的“同一性”依舊是黑格爾同一性邏輯的世俗化的翻版,它與歷史唯物主義高度重視的“非同一性”邏輯并不吻合,甚至還可能產生一定的偏離。資本邏輯的闡釋雖然能夠較好地在現代世界何以建立的各種說法中(技術說、理性說、新教倫理說等)獨樹一幟,但是,它僅是作為現代世界的資本主義通行原則。如果我們僅僅看到這一點,《資本論》便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生存寶典,被設想為資本主義危機之后的一次又一次的復興。歷史唯物主義絕不僅如此,它還更多地指向人之解放,解放是一個新人的創造過程,一個逐漸脫離資本邏輯的過程,一個挖掘資本邏輯同一性受到重創的過程。誠如霍洛威(John holloway)所說的,需要我們不斷去尋找資本同一化的裂縫,這是人類逃離資本主義的希望。
資本邏輯批判易于將人作為客體
歷史唯物主義的出發點是現實的個人,資本邏輯批判闡釋的出發點卻是“丟失”人、“否定”人的資本世界。我們每個人在資本的世界中不可見的與可見的盡是資本、交換、商品等一系列價值形式,在以往的《資本論》解讀中,這成為了基本的理念。誠如馬克思確實描述了現代個人的位置,他們在“受抽象統治”下生存,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遮蔽。人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始終是匱乏的狀態,不斷地努力通過商品交換世界來填充這種無盡的匱乏。我與商品世界之間的“主客關系”徹底顛倒了,我成為了一個作為主體的商品世界的“客體”存在。
但是,馬克思實質上并不僅在于對資本世界建構的邏輯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對資本世界的逃離,追求走向一個祛拜物教化的、祛資本邏輯的世界。可惜的是,我們今天已經將資本邏輯闡釋為一個自治的世界,忘卻了這個世界正是我們自己建構的,消除資本邏輯世界的真正根源在于我們是如何建構的。
用霍洛威的看法,正是從拜物教思路出發,即使我們設想的讓無產者聯合起來去打破資本邏輯的解放策略,也依然是將無產者作為“客體”來考察。所以,任何將人作為“客體”對待的思維都與人的解放的思考相距甚遠。那么,從商品出發永遠擺脫不了將人作為“客體”這一困境。為此,霍洛威進一步提出的設想是,“我們打算做的事情要以有助于促進自己與其他人相關的創造方式,而不是跟隨貨幣的邏輯,不是跟隨資本主義的模式”。這是擺脫商品自治世界的唯一道路。當然,霍洛威的想法不在于是否能夠徹底全盤地打破資本世界,其價值在于,他突破了資本邏輯闡釋這條“流行”的規律,看到了資本邏輯自治的缺陷,以此告訴人們,一旦我們從否定人、將人作為客體來加以對待人的時候,人的解放從思考的那一剎那就已經錯失了方向。
資本邏輯批判的修補
那么,要對資本邏輯進行修補,絕非要廢棄資本邏輯的闡釋視角,而是認為它僅僅是歷史唯物主義切入當代社會的分析視角之一,它的限度十分明顯。雖然它在總體性的意義上把握了這個時代,卻無法讓顛覆資本邏輯的解放維度在當下出場,這樣便是我們所經常聽到的:解放還可能嗎?由此,對資本邏輯修補就是要將解放的維度融合進去,這一個維度便是立足人的勞動而展開的。
我們知道,當下的勞動表現為價值形式,這是資本邏輯最為核心的議題。可是,那些立足勞動時間與價值的比例關系的證偽者不得要領地否定勞動價值論,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因而,勞動與資本的對立也便是幾百年來資本主義的“秘密”,朝向資本的戰斗也曾有過,但是,今天人們已經開始講述資本的文明價值了,這是資本生產力迷戀的結果。真正推動生產力的根源是應該回到勞動本身的方式上加以設想。可是在拜物教的視野下,人們已經無法想象沒有資本如何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仿佛資本成為了生產發展的唯一鑰匙。
回到根源上看,資本作為死勞動壓制著活勞動,換句話說,活勞動受著自身勞動的壓制,因為我們的勞動指向了價值,被價值所吸納。一旦如霍洛威所展示的,當我們將活勞動不再朝向價值生產,而是在價值生產之外,尋求一點屬于自己生命豐富性、創造性的勞動領域的時候,資本邏輯的鏈條便斷裂了。于是,今天要提升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的價值,就需要努力挖掘勞動的非價值導向,重塑勞動對人自身豐富性、創造性的提升。只有這樣一條道路在歷史唯物主義的關照下被健康地開掘出來,才真正匹配于人類新型文明道路的創生。因而,利用“勞動的生產力”而不是“資本的生產力”,所謂前者即高度關注人與人之間的非異化的社會關系的合作力量,諸如共享式的維基式的知識生產模式,而后者則是以物與物的異化了的社會關系作為社會建立力量,資本成為了生產力的核心要素。
說的更直接一點,立足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邏輯批判進行修補的重要任務是,重新構建新型的勞動合作模式,提升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化”維度,降低乃至逐漸消弱資本生產力的任務。相信這一課題的深化,不僅會在理論上刷新人們對歷史唯物主義解放理念的認識,同時也將使中國道路為人類新型文明所做的探索提供智力支撐。
孫亮,1980年10月生,現為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系博士生導師,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研室主任。兼任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文化研究院研究員。2014年起在南京大學哲學系從事博士后研究。德國耶拿大學訪問學者(2015-2016)。主要研究:德國哲學、馬克思文本、國外馬克思主義。近五年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兩項,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兩項,另外主持上海市、中國博士后等省級科研與教學課題五項,獨立在重要期刊發表學術論文六十余篇,其中二十余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等二次文獻全文轉載。出版專著、譯著五部。曾獲得教育部優秀博士生學術新人獎、寶鋼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2017年入選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2017年主講課程被評為上海市精品課程。
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567期第5版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