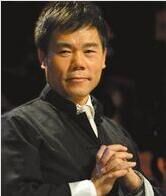值此日本投降紀念日,小編重發戴旭老師舊文《戰勝中國——日本百年不易的夢想》一文,銘記歷史 吾輩自強!
以下是正文:
【按】: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自導自演了一出從日本私人手里“購買釣魚島”的事件。大多數中國人將此視為針對中國的“9.11”事件。中國反日情緒迅疾燃遍全國,雙方國民互增惡感。日本則依然我行我素,政治家一個個比著對華強硬,野田首相靠制造釣魚島話題連任后竟然到聯合國公開日本對釣魚島的主張,而另一位日本外交官卻搬出《馬關條約》證明日本的主張。堪稱對華第一鷹派的前日本外相前原誠司,被野田內閣啟用為戰略擔當相。此人還未上任,就攻擊中國“ 極度歪曲歷史。中國是個一貫偽造自己歷史的國家”。 2012年國慶,中國領導集體赴天安門廣場朝拜人民英雄紀念碑。中日兩國未來關系的主動權,百多年來一直掌握在日本手里。日本對于中國,每個歷史時期的策略都有不同,但基本戰略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雙方今后關系及各自命運如何,并不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歷史曾經不止一次地路演過。現在,讓我們回過頭去,簡略地打量一下日本近代至今的戰略思想軌跡。
生為中國人,幾乎就注定無法避免與日本發生各種各樣的糾纏。無論是關于歷史還是未來的話題,也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或者是軍事領域,無論你是政治領袖還是企業家,無論你是軍人還是平民,認識日本,研究日本、了解日本,都是中國人的一種生存必需課。如果再進一步——戰勝日本,則有這種意識和志向的中國人,其數量和質量,將可以作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標志。
近百年前,中國軍事戰略家蔡鍔說,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必須邁過日本這道坎。今天,中國仍然被擋在這道坎前頭舉步維艱。
一、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動力之一是“直陷北京城”,“蹂躪支那”
在世人印象中,日本是善模仿而不善思考的民族。但自一百多年前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不僅政治、經濟、軍事發生了全面變化,其思維方式也有了脫胎換骨的改變。領導這一社會變革的青年武士,提出“殖產興業,富國強兵,文明開化”的口號,以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財團產業群隨之產生,在此基礎上,日本采取“開拓萬里波濤,揚國威于四方”的軍國主義政策——名為“四方”,其實只是西方,即中國及其周邊所屬勢力范圍。
地理上一衣帶水,生理上一脈相承的宿命;兩千年中中國領先世界一千八百年的歷史事實,讓日本無可選擇地成為中國文化的學習者;無所不在的“中國”熏陶濡染,又固化成日本一種恒定的心理,即自覺自愿地自以為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南宋被蒙古征服,君臣軍民崖山集體蹈海,日本為之舉國戴孝,認為中華正統文化已滅,東瀛成為中華文化余脈。晚清中國改革失敗,革命興起,日本先是保護康梁立憲派,后來又全力協助中華革命黨人,并先于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至今,中國原藩屬國越南、朝鮮半島俱已廢除漢字,唯日本對漢字珍視如初。
地理、生理、心理,使日本與中國糾結出復雜的“血緣關系”。世人但知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蠶食鯨吞,豈不知,日本卻視并吞中國為地理、生理和心理的回歸。相當程度上,受這種“血緣關系”的支配,日本始終有一種登陸靠岸、西進中國的莫名動力。
自中國明朝后期,日本戰略家豐臣秀吉就計劃以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他制定征服朝鮮、占領中國,進而奪取印度的侵略藍圖,并于1592年和1597年兩次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豐臣秀吉雖然沒有如愿,但他的思想,卻成為日本近現代戰略文化的根源。
此后四百余年,日本處心積慮“謀華”。1823年佐藤信淵寫了《宇內混同秘策》,明確把侵略中國的東北作為第一目標。明治維新后,每發動一次侵略戰爭,日本軍方就把佐藤信淵的書重印散發,作為軍人必讀教材。
日本明治時期戰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澤諭吉。他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 晚年成為一個狂熱的軍國主義者,主張侵略朝鮮,進攻中國。他說:“自己去壓迫他人,可以說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躪支那帝國四百余州”。1884年福澤諭吉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東洋的波蘭》一文,認為15年后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理所當然地占據臺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并刊載了一份瓜分中國的預想圖《支那帝國分割之圖》。1885年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論,認為“現在的支那(中國)、朝鮮于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朝鮮,亦無須特別客氣,竟可效仿西洋人處之”。福澤諭吉之武士道精神,深印在許多日本人頭腦之中,影響日本社會各個層面,直至今日,還是一萬日元上的頭像。
1927年的《田中奏折》幾乎就是《宇內混同秘策》和福澤諭吉思想的具體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中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東亞為中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這個奏折確定以美、蘇為假想敵國:“然欲以鐵與血主義實保中國東三省,則第三國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來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擊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中國為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將來在北滿地方比與赤俄沖突。” 奏折還大肆歪曲歷史,否認中國對滿蒙之主權:“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區域”“中國此后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以新其大陸。”
日本終于等到近代清朝衰落遭遇西方入侵,而日本憑借“明治維新”成功,遂于1879年正式并吞中國藩屬琉球國。之后,日本舉國上下以征服中國為統一意志。政治家縱橫捭闔、趁火打劫;實業家以發展工業充實軍備;軍隊為伺機發動戰爭準備各種方案......狂熱的日本年輕人喊著要和中國打百年戰爭,或受命或自發投入到征服中國的“事業”中。
二、甲午戰爭時日本已萌生吞并全中國之念,小學普及陸軍大學教材
甲午戰爭1894年在中國東海打響,而之前日本間諜已深入中國湖南湖北云南廣西,為日本搜集中國全面情報)。1889年4月,年輕的間諜荒尾精向日本參謀本部遞交有關中國大勢的分析報告,認為大清國“上下腐敗已達極點,綱紀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業殆盡傾頹”,認為西方必將瓜分中國,這樣又將會牽連日本。他建議日本“先改造中國”,然后“團結中國”對抗西方。另一位間諜宗方小太郎,1895年分析《中國大勢之傾向》。當時東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國即將崛起,以中國之豐富物產,如能積極變革,則"成為世界最大強國,雄視東西洋,風靡四鄰,當非至難之也”,但宗方小太郎認為中國雖然表面上在不斷改革和進步, 但大清全民都腐敗,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跡象,“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經不起大風地震之災”,早則十年,遲則三十年,中國“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見雪珥《絕版甲午》)。這些報告促使日本決心向中國開戰,以效法元、清故事。
1906年,日本參謀本部陸軍大尉日野強,接到前往中國新疆“視察”指令。日野強坐車、騎馬、徒步、乘船,自河北經河南、甘肅,入新疆,沿哈密、吐魯番,翻越天山進入烏魯木齊,經綏來(今瑪納斯)、庫爾喀喇烏蘇(又稱西湖,今烏蘇)前往北方邊鎮塔爾巴哈臺(今塔城) ,而后返回到庫爾喀喇烏蘇再折向伊犁,然后又獨自翻越天山,到達位于天山南路東部的喀喇沙爾(今焉耆),然后沿天山南麓西行,經庫車到阿克蘇,入喀什噶爾(今喀什),然后經由英吉沙,前往葉爾羌(今莎車)。1907年9月離開新疆進入印度,由海路返回日本。歷時一年零四個月,日野強寫下厚厚兩卷的《伊犁紀行》,分為為地勢、風土、居民、風俗、宗教、教育、產業、交通、行政、兵備、歷史概要、俄國人在新疆的現狀、新疆所感。附錄“新疆瓊瑤”還錄下了當地官員文人贈給他的詩作。其中“地勢”一章又分地理位置、廣袤、山脈、河流、湖澤、沙漠、居民點等;“居民”一章下分人口、人種,及纏、蒙、漢、滿、回、哈等民族各條,又于“風俗”和“宗教”兩章下分食、住宅庭園、婚喪習俗、節慶禮儀、歷法文字、男女及家庭關系、喇嘛教(藏傳佛教)、回教(伊斯蘭教)、基督教、民間道教等內容,在“產業”、“交通”兩章中,介紹有關農林、工商、礦產、畜牧各業以及道路通訊等設施問題,在“行政”、“兵備”等章中介紹行政體系、財政、軍備的狀況。
日野強的故事,形象地說明日本是多么地精心、認真準備征服全中國。知彼的功夫下到這種程度,知己的功課做的更好。甲午戰爭前,日本陸軍參謀局的漢學家、史學家中根淑編寫了一部《兵要日本地理小志》,專講日本山川險要、地理、氣候、人情、風俗、政治、歷史、物產、戶口以及戰史、戰場等,“其如攻守要害,以古人勝敗明辨其地勢,使古今之沿革戰斗詳然如指掌”。在這部日本國第一部軍事地理志的序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此書本為陸軍軍人課本,而今為小學課本。”“今也兵農一途,舉海內皆兵。小學生徒能讀此書,詳山勢水脈險夷廣狹,則他日或從兵事,攻守進退之劃策,有思過半矣。然則此書名為地志,實兵家之要典,而小學生徒不可闕書也。”
世人但知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實現在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和軍事強大,而沒有覺察其實日本最大的變化,乃在于對全民進行了思想武裝。讀著《兵要日本地理小志》長大的日本兒童,很快就成為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急先鋒。
石原莞爾還是在關東軍中佐的時候,就憑借自己的戰略理論,判斷出將會發生一場決定世界命運的戰爭,戰爭的原因是東方精神價值和西方物質價值的沖突。石原先是把美國看作決戰的對象,后把蘇聯看作眼前的對手。為此,他認為憑日本的國力是不足以戰勝美蘇的,為此必須征服中國,以利用中國的人力和物力資源。占領東三省只是他計劃的第一步。這種思想正是荒尾精的基本主張。石原莞爾被稱為關東軍的“大腦”。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曾有人評價說,石原莞爾的頭腦是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的頭腦”。1922年,他留學德國,研究過拿破侖軍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他的全部興趣和愛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與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形成團伙,策劃發動“九一八”事變。
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后,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即化裝偵察。“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前哨戰。他們在哈爾濱、錦州、旅順等地制定了日軍在這些地區作戰的攻防戰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占領滿蒙的計劃,并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系”。
在日本上述思想軌跡后面,是日本軍隊鐵蹄在中國留下的血跡:1879年并吞琉球——1898年割占中國臺灣,澎湖各島——1900年,日本參與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搶劫——1904年,日本進入中國東北,奪南滿,旅順,遼東,迫使清朝開放鳳凰,遼陽,鐵嶺,長春,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滿洲里等十六城供日本人居住——1914年,日本奪占中國膠東半島青島,濟南各城,迫袁世凱同意簽署“二十一條”,初現滅亡中國之野心——1927年,日本出兵青島、濟南阻止北伐軍進兵。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日本天皇奏折稱:“吾人如欲征服中國,則必先征服滿蒙:吾人如欲征服世界,則必先征服中國:吾人如欲能征服中國,則其余所有亞洲國家及西洋諸國,均將畏懼于我,臣服于我”——1928年六月,日軍在沈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1931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軍攻占東北軍北大營,占領東三省——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挑起淞滬戰爭——1932年三月九日,日本宣布偽滿州國成立,1933年一月,侵占山海關,熱河,長城及冀東地區——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隊在北平盧溝橋發動七,七事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1937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占南京,制造大屠殺事件——1938年,日本侵占冀中,魯南,青島;攻占徐州地區,廈門、廣州、、漢口、岳陽——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島及汕頭;轟炸重慶——1941年十二月,日本攻占香港........
三、《戰勝中國》:日本對中國也有一個C形包圍計劃
受征服龐大中國使命的驅使,對中國社會情勢的全面分析,對中國的各種戰略研究,對日本自身境況的分析對照,從此形成一種社會自覺。這種集學術研究、政治和軍事戰略于一體的習慣,一直延續至今。1997年,當時名列世界五百強第一的日本財團“三井物產”,旗下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市川周出版了一本書,名叫《戰勝中國》。此人提出日本對中國要有“競爭對手意識”,要充當“戰斗的(東亞)家長”,海洋國家(日本)要與大陸國家(中國)對抗,要利用“非華人對華人感到的壓力”,廣泛團結非華人國家對抗中國大陸。市川周在書中把亞洲分為三個區域:第一是東亞海洋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臺灣及東海釣魚島;第二是中國大陸;第三是南亞及中亞蒙古等中國周邊國家。市川周進而提出,日本要采取確保第一區域,影響第三區域,包圍第二區域的戰略,其核心框架是“東亞共同體”。
市川周推崇的日本古代人物是圣德太子(推古天皇時代的攝政,實際掌握政權),他是日本史上著名的對外擴張先驅。607年圣德太子給隋煬帝的國書的開頭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市川周指出,“圣德太子完全沒有本國地位卑下的意識,……他以在所居住的斑鳩宮的遼闊的上空鳥瞰中國大陸、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列島的感覺,從而產生了寫下以上開頭的念頭。” 市川周全面認同福澤諭吉“脫亞入歐、吞并中國”的主張,認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對外擴張在開始的很長時間里都比較順利,關鍵是是“日本托身于歐美列強勢力庇護下的‘自存自衛’。”其本質是英美扶植日本對抗俄國和中國,無論是1894中日戰爭還是1904俄日戰爭,其背后都是英美,一戰前后日本與德國爭奪中國青島,其背后還是英美,1931年日本發動918事變吞并中國東北,其背后還是英美。歷史的轉折點發生在1939年前后。1937-1939年,由于中國共產黨敵后抗日根據地的蓬勃發展,使日軍深陷中國戰場。日軍不得已向北突進,1939年日本進攻蘇聯遭遇“諾門坎慘敗”,因此決定冒險南下與美國開戰,這就是兩年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最終結果是4年后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日本在二戰中的失敗,主要原因是自己軍事力量不夠時,貿然對英美軍隊發起全面戰爭。諾門坎事件的失敗已經證明日本無法打敗蘇軍,但是日本沒有認真總結、檢討,并積累力量,反而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與美軍全面開戰,是日本的最大失誤。因此,市川周認為今天的日本,在總結二戰教訓所形成的對外戰略只能是:1、密切與美國的關系,依附在美國身上,擴充經濟、軍事實力,實力不到時,絕不與美國對抗。2、依靠美國的力量,繼續向中國、俄國方向擴張。(普京上臺以來,俄羅斯似乎敏銳地觀察到了日本二戰后的戰略動向,因此普京以來,俄國在北方四島問題上對日本十分強硬,在強硬的俄國無法突破的背景下,日本必然選擇向中國方向擴張。這正是近年來日本在釣魚島事件上對中國一再挑釁的原因。筆者屢次堅決主張打退日本戰略挑釁的原因,也是看到了這一點。)
今天的日本和1895年的日本沒有本質區別。眾所周知,日本各屆政府及主流社會輿論對靖國神社里甲級戰犯靈位的推崇、崇拜、祭奠,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歷史問題和民族感情問題,其本質是鼓勵當今及以后的日本軍人和國民繼承軍國主義精神對外擴張。20世紀80年代,出于對抗蘇聯霸權的需要,中美-中日之間曾有短暫的蜜月期,中日建交時,日本政府曾答應擱置釣魚島爭議,整個80年代,釣魚島問題沒有惡化。然而,蘇聯解體后,中美關系惡化,日本也積極參與到瓜分和肢解中國的進程:90年代日本開始加快落實侵占中國釣魚島的步伐,比如兩次建立燈塔并樹立帶有日本國旗的木碑;日本政府拋出“臺灣問題未定論”,扶植臺獨;日本政府邀請達賴十幾次訪問日本……等等。明治維新后,日本的脫亞入歐是參與舊殖民主義秩序,瓜分中國。今天日本的脫亞入美(歐)則是參與新殖民主義秩序,繼續瓜分、肢解、控制中國。
市川周主張的“戰勝中國”之戰略,首先是在經濟上戰勝中國。十多年以來,東盟與日本之間的經濟整合日益加深,在這期間日本確實也加強了對東盟各國的技術轉移。由于日本工業擁有強大的技術優勢,第一區域各國的經濟很容易被日本所整合。最近,連美國也摻和進來搞排除中國的TPP,其實這是由美國的金融、軍力加日本的工業實力組織起來的反華聯盟。中國雖然積極地推進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但90年代以來中國發展的很多經濟產業與東盟國家是競爭關系,在這一點上中國不占優勢。東盟各國都警惕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日本的戰略意圖是用工業技術實力彌補其政治層面的不足。
2006年日本另一位戰略學者松村劭,發表《海洋國家日本的軍事戰略――對照戰史則防衛政策課題自然明了》,主張與市川周如出一轍。此文要點有五:一,當今世界處于海洋國家對大陸國家的包圍態勢中,由于美國作為“海洋國家”擁有絕對軍事優勢,日本應該謀求建立類似跨大西洋的美英關系那樣的,跨太平洋的“對等的日美軍事同盟”,加入美國這一強勢陣營;二,歷史上西歐列強從太平洋進入中國大陸的最佳途徑是取道臺灣,作為重要貿易航路巴士海峽兩翼的臺灣和菲律賓,日本必須格外重視;而扼守馬六甲海峽的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日本也必須將其作為與臺、菲一樣的“優先友好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南太平洋的“海洋國家”,因而也是日本的“同盟對象”;三,日本應巧妙離間中俄,盡可能地推動中俄戰略對立和對抗;四,如同東歐是西歐與俄羅斯之間的“緩沖地帶”一樣,對日本來說,朝鮮半島和越南也是日本與中俄之間的“緩沖半島”,日本必須聯合美國防止中俄在這個緩沖地帶擁有軍港、航空基地和(核)導彈基地;第五,提防中國從經濟大國走向軍事大國。松村劭主張:日本的國家戰略應是一種“西太平洋戰略”,即通過以上措施,實現日本作為西太平洋海上強國的再次崛起。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中央最高層終于拍板高考大變革方向!中國
中央最高層終于拍板高考大變革方向!中國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