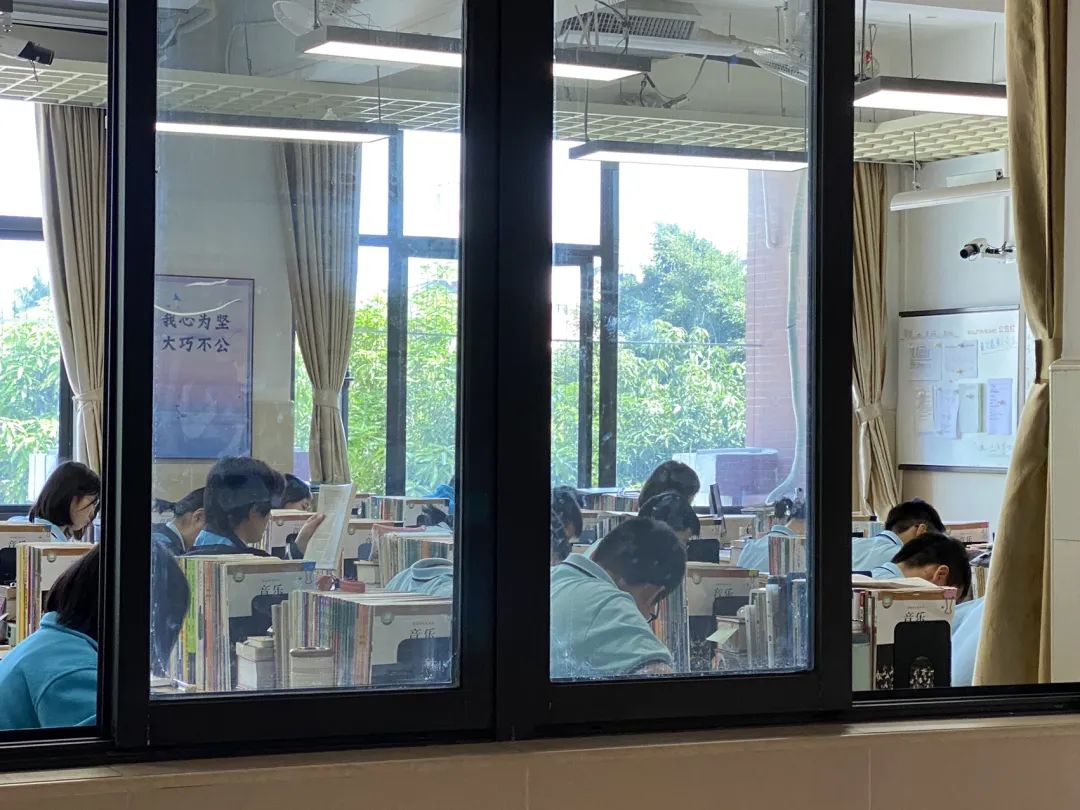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2周年的日子里,蘭考老同志滿懷深情地回憶起當年傾力做好紀念焦裕祿的三件事,仍然是心潮澎湃、激動不已。
一、焦裕祿的陵墓是怎樣遷回蘭考的
焦裕祿臨終前對張欽禮說:“欽禮,我的時間不多了,有句話我不能不說了。……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丘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張欽禮知道,這是即將離開人世的焦裕祿留下的托付之情。他飽含著對未竟事業的牽掛,飽含著對蘭考這方熱土的萬分留戀,也飽含著對張欽禮的無比信任。焦裕祿臨終時推心置腹的話語刻在了他的心上,成了張欽禮念念不忘的夙愿、割舍不掉的情結和改變蘭考貧窮面貌的強大動力。為了早日實現焦裕祿的遺愿,張欽禮思索著、嘗試著、努力著。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張欽禮乘河南掀起宣傳學習焦裕祿高潮之機,親自跑到河南省民政廳請示這件事,當面向民政廳施廳長陳述了焦書記的臨終囑咐,施廳長聽了十分感動。但鑒于上級就地安葬的有關規定和當時組織上已將焦裕祿安葬在鄭州的現實,再遷墳已不可能。張欽禮十分理解地離開了省民政廳。但他并不甘心,因為這是焦裕祿臨終的囑托,這里體現著一種精神,這也是他對焦書記當面點過頭,答應過的事情。一九六五年五月焦裕祿逝世一周年之際,蘭考縣出席河南省貧代會的二十六位代表,買了一個大花圈,乘著大會秘書處派的大轎車,前往鄭州烈士陵園悼念焦裕祿。陵園內烈士墓一大片,每個墓前有一個小石碑,刻著烈士的名字。代表們一下車,在陵園內抬著花圈,流著淚到處尋找。突然,有人喊道:“快來呀,焦書記在這兒!”大家一齊向焦裕祿的墓跑去。他們向焦裕祿的墓敬獻花圈,然后撲通撲通地跪趴在焦裕祿的墓前,痛哭不止。他們抱碑拍墓,呼喚伴隨著淚水在風中飄蕩。隨行的樊哲民、劉俊生含著淚勸大家:“別哭了,快開會了,回去吧!”老貧農張傳嶺痛哭失聲,說:“焦書記為咱操心,跟著咱蘭考受苦。如今咱的日子好過了,他卻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這兒……”一語未了,樊哲民、劉俊生和大家一齊痛哭起來。最后,為了不影響開會,幾個隨行的人員把他們連拉帶抱地拽到汽車上。車開了,車廂里仍是一片抽泣聲。這件事著實讓張欽禮感慨萬千。他理解蘭考人對焦裕祿的這份感情,他在心里默默地說:“蘭考人懷念焦書記,還得跑到鄭州,那么遠,多不容易,多不方便啊!”這時,焦裕祿臨終時的囑咐又響在他的耳邊,他的淚忍不住地一滴滴掉了下來。蘭考縣二十六位代表到焦裕祿墓前哭祭的事,更加堅定了張欽禮為焦裕祿遷墳的決心。機會終于來了。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長篇通訊,一個學習焦裕祿的高潮在全國興起。再加上穆青、周原有建議,蘭考人民有要求,張欽禮要借這個東風來實現焦裕祿對他的托付之情。一天,張欽禮指著窗戶外面一堆堆、一團團的人,問卓興隆:“老卓,你說那么多人來咱這兒,都看什么呢?”“反正不是看你看我的。我太胖,你太瘦,沒看頭。”卓興隆的幽默是出了名的。“你看,學習焦裕祿這么大的陣勢,可咱焦書記的墳都不在蘭考。我們能不能像諸葛亮借東風那樣……”沒等張欽禮把話說完,卓興隆心領神會地笑了,說:“聽你這話的意思是,焦書記的墓地在鄭州,咱蘭考群眾悼念不方便,來蘭考參觀的人想看看焦裕祿的墓還得跑到鄭州。咱去跟省委說說,請求把焦裕祿的墓遷回蘭考!”張欽禮笑了,說:“知我者,卓興隆也。”于是,張欽禮以縣委的名義向省委起草了一份遷墳報告。他叫上卓興隆,帶著報告,帶著穆青、周原的建議,帶著蘭考人民的重托趕到河南省委,請求將焦裕祿同志的遺骨由鄭州遷回蘭考安葬。張欽禮找到省委劉建勛書記,劉書記同意了蘭考縣委的請求。張欽禮心中很激動,說:“得有個手續吧!”劉建勛對紀登奎說:“給他們辦一辦吧!”紀登奎當下就批準了蘭考縣委的請示,并派人通知鄭州鐵路局密切配合,備好火車專列。蘭考的沙丘很多,安葬在哪里為好呢?縣委經綜合考察研究,最后確定:焦裕祿陵墓建在縣城北邊黃河故堤的沙丘上。一是這里離縣城近,便于瞻仰管理;二是當年焦裕祿查風口時,曾站在這兒幽默地對張欽禮說,“這里站得高,看得遠,可以觀察到沙起沙落……今后我死了,可以埋在這里。”焦裕祿墓地確定后,張欽禮親自掛帥,積極做好遷墳的各項準備工作。正在這時,鐵道部下發了“從三月一日起,禁止用火車運尸體”的通知。為此,焦裕祿的遷墳工作必須在二月底前完成。時間緊,任務重,張欽禮帶領大家連天加夜地干,縣直機關和聞訊的蘭考群眾踴躍參加義務勞動。人們為迎接他們敬愛的焦書記回蘭考忙碌著,興奮著……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遷葬工作開始。這天上午,在鄭州市烈士陵園舉行了起靈儀式。省委劉建勛書記帶領參加省三級干部會議的各地、市、縣負責同志參加了儀式并講了話。起靈儀式結束后,焦裕祿的靈柩用汽車運到火車站,移到早已備好的火車專列上。鄭州鐵路局派出的火車專列共四節車廂。一節是省、地市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一節是靈柩和護靈的焦裕祿家屬等人員;一節是國棉三廠的軍樂隊;一節是花圈和工作人員。火車頭前邊掛著焦裕祿同志的遺像,系著黑紗。車廂兩旁貼著“向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同志學習”的巨幅標語。
一個縣委書記去世,國家動用專列運靈柩,這在中國歷史上當屬先例,也是當時焦裕祿最大的殊榮。火車從鄭州出發,中午十二點左右到達蘭考。在一片哀樂聲中,焦裕祿的靈柩從火車上移到汽車上,由送靈人員陪護著緩緩駛出火車站。此時,蘭考的火車站廣場和大街兩旁肅立著迎靈的人們。蘭考縣委、縣人委的領導胸戴白花,臂戴黑紗,滿懷深情地和廣大人民群眾一起迎接他們的好書記焦裕祿。成千上萬的人民群眾看到焦裕祿靈柩的到來,有的默默流淚,有的痛哭不已。在痛哭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農民孔令煥的妻子,她抱著被焦裕祿救活的孩子,一直攆著靈車哭喊,還有紅廟公社張全德的妻兒老小……哭聲感天動地,在蘭考上空久久回蕩。

中共蘭考縣委在焦裕祿墓地舉行了隆重的安葬大會。據當年《河南日報》報道:參加追悼會的有五、六千人。墓前搭起了牌樓,牌樓兩邊寫著:“揮淚繼承壯士志,誓將遺愿化宏圖”;上面的橫額寫著“焦裕祿同志永垂不朽!”
這四面紅旗是焦裕祿同志生前在蘭考樹立起來的。這四桿旗,在過去三年蘭考人民改變自然面貌的斗爭中曾經發揮了巨大作用。現在蘭考農村的紅旗單位已經增加到十個,他們是蘭考人民今后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榜樣。

焦裕祿與世長辭后,他的老同事和蘭考人民化悲痛為力量,為根除“三害”、造福百姓,殫精竭慮、艱苦奮斗,使蘭考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張欽禮在安葬大會的悼詞中宣告了這一變化:一、風沙治理的情況:造林防沙,百年大計;育草封沙、當年見效;翻淤壓沙、立竿見影。三管齊下,在二十萬畝沙荒地上造上了防風固沙林。造林樹苗全是自己采種、育苗。全縣兩千五百七十四個生產隊,隊隊有苗圃,一年成苗達三千多萬株。根據樹木習性科學種植,種管結合。使沙灘、沙丘、沙龍披上了綠裝。又因防風固沙林為農田支起了護衛屏障,有效防止了風起沙飛打壞莊稼,使農田年年季季都有較好收成。二、澇災治理的情況:蘭考地勢西高東低。全縣主要分為黃蔡河、賀李河、惠濟河三大排澇系統。還有配套的干渠、支渠和黃河灘區的排澇水系。凡是有關省界、地界、縣界和公社界的河道為縣管河道,由縣統一組織力量、按二十年至三十年一遇的排澇標準開挖排澇河道。三年共挖土方二千七百萬立方米。公社以內的排澇河道由各公社統一組織人力、物力,按十年到二十年一遇的排澇標準開挖。大隊、生產隊負責溝、渠配套。全縣形成了一個系統的排澇泄洪網絡。三、鹽堿地治理情況:蘭考系黃河沖積平原。俗話說,水堿一家。河道通,鹽堿輕。加之以沙壓堿、修筑臺田、深翻土地、開溝躲堿,以及種植耐堿作物等,使鹽堿地得到了有效治理。全縣在堿地上種的五萬畝高粱,平均每畝產三百多斤。一九六五年,全縣基本沒有發生堿死莊稼的災害。全縣年糧食產量達一點六億斤,人均四百四十斤。與一九六二年相比,糧食增產一億斤;人均增產二百七十四斤。最后,張欽禮在焦裕祿的靈前含淚宣布:“我們向上級立的軍令狀提前實現了!我們除‘三害’三年規劃勝利完成了!這是三十六萬蘭考人民學習你的精神、艱苦奮戰的結果。焦書記,你可以瞑目安息了!”此語一出,頓時會場一片歡騰、一片哭泣。“向焦裕祿同志學習!”“焦裕祿精神永垂不朽!”“焦裕祿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口號聲此起彼伏。悼念會上,大家群情激昂,熱血沸騰。焦裕祿同志的安葬大會變成了學習焦裕祿精神、徹底改變蘭考面貌的誓師會。這天,最激動的人要數張欽禮了。他完成了焦裕祿的臨終囑托,也了卻了自己的一樁夙愿。他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心里輕松了不少。后來,時任國務院高教部部長、原河南省委第二書記何偉同志,從北京趕來參觀焦裕祿事跡。這是他第三次光臨蘭考。張欽禮、潘子春、卓興隆、樊哲民等同志陪同何偉部長到農村走一走,看一看。那七十里長、五里寬的北沙河綠色長城,那九米九、下馬臺等許多沙丘、沙龍、沙灘披上的綠裝,那二十多萬畝的防風固沙林,讓心系蘭考的老領導感動不已。他說:“蘭考真成了林的世界。”在視察賀李河流域時,那里的群眾告訴他,自從開挖了賀李河,蘭考東半縣、民權西半縣、山東曹縣西南一帶的澇災區再也沒有淹過,年年都是好收成。水利糾紛沒有了,群眾有吃有穿了。何偉書記視察了堿地的治理情況,還親自到焦裕祿樹立的典型秦寨大隊看望那里的群眾。人們告訴他,如今他們吃穿不愁,不僅超額完成了向國家交的公糧,還有了自己的儲備糧。何偉在蘭考視察了三天,三天都在激動中度過。特別是聽說蘭考人大都能吃上大米、白面,連過去窮得讓人直搖頭的許貢莊都成了富裕村、樣板隊,心中十分欣慰。他又想起昔日那個連大米也沒有見過的孩子,他又一次流淚了,這是喜淚呀!最后,何偉來到焦裕祿墓前。他深深地向焦裕祿鞠了三個躬,動情地從口袋里掏出一小瓶竹葉青酒,在焦裕祿靈前來回澆了三行,語重心長地說:“焦裕祿同志,我用激將法考驗過你和欽禮同志,你們立了軍令狀。為了實現除‘三害’規劃,你活活累死了,張欽禮和縣委一班人是脫了三層皮,你們是前仆后繼呀!焦裕祿同志,你圓滿完成了上級交給的任務,你的死重于泰山!”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在全國引起很大震動,每天到蘭考學習焦裕祿的人成千上萬。為了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時任學習焦裕祿委員會主任、縣委副書記張欽禮提出,創辦焦裕祿革命事跡展覽館。蘭考縣委研究決定,抽出縣委辦公室劉俊生、王保華負責創建工作。一天,兩人請示張欽禮:“怎么籌辦焦裕祿事跡展覽館?”張欽禮說:“舉辦焦裕祿事跡展覽館可分兩步走。第一步先辦個臨時性的,第二步縣委研究后再辦個正規的。”王保華問:“臨時性的怎么辦?”張欽禮答:“我叫除‘三害’辦公室的同志繪一些圖表,統計好數字。你們搜集些焦書記的遺物,匯總焦裕祿的事跡、報刊、文章等資料……咱先辦起來,再完善。”又對劉俊生說,“你拍的咱焦書記的照片太珍貴了。還有你拍的那么多治理風沙、鹽堿、內澇的照片,寫的那么多紀念文章,都能派上用場。那是咱焦書記帶領我們改變蘭考貧困面貌的真實寫照,都搜集起來辦展覽用。”于是,劉俊生連天加夜找資料,翻箱倒柜找照片。他給焦裕祿拍的那幾張照片確實珍貴。其中焦書記在花生地里勞動的照片,后來被中國郵電部作為紀念郵票在全國發行。蘭考當時攝影者少,照相機又不普及,當年“焦展”的絕大部分照片都是劉俊生拍的。人們說,劉俊生拍的照片是“焦展”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根據張欽禮的意見,劉俊生、王保華起早貪晚地辦起了焦裕祿事跡臨時展覽館。地址設在縣機械廠十多間廠房內,又從縣、社、機關抽調十多位青年女職工當講解員。開館的第一天,講解員試講。張欽禮和卓興隆最早來到展覽館聽講解。張欽禮充分肯定了焦裕祿展覽館的創辦工作,對講解員給予了熱情的鼓勵,并提出要求:“你們介紹焦裕祿事跡,首先要帶著深厚的階級感情去講。要著裝整齊,講普通話。說咱蘭考的土話,外面來參觀的人聽不懂。”卓興隆說,“咱蘭考把明天說成‘趕明兒’,現在說成‘要會兒’,連翻譯都聽不懂。頭搖得像撥浪鼓、臉憋得通紅也翻不出來。”說得大家哄堂大笑。焦裕祿臨時展覽館的開放,一傳十、十傳百,引起人們的熱情關注。多新鮮哪,蘭考人自己辦“焦展”。雖然土些、簡單些,但畢竟是全國第一個啊!參觀的人都懷著崇敬的心情來學習焦裕祿。展室內有一張焦裕祿在農村睡的床鋪,上面鋪些干草。一位來參觀的青年說:“焦裕祿愛蘭考的一草一木,我們學習焦裕祿,也愛蘭考的一草一木。”他掐了一根草,夾在日記本里作紀念。其他人也跟著這樣做。不長時間,床上的草幾乎被掐光了……在張欽禮的關切和重視下,蘭考臨時“焦展”辦得有聲有色。他們還到外地參觀學習了辦館經驗。為了進一步辦好“焦展”,縣委分工除“三害”辦公室主任卓興隆抓焦裕祿革命事跡展覽館,又選拔了一些政治素質高、熟知焦裕祿事跡、又有業務專長的人員到“焦展”工作。他們在距縣委百米遠的一片十二畝大的空地上,建起了比較正規的展覽館。展覽內容是按照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版本興辦的。興辦時正巧廣州美術學院畫家惲沂倉(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的侄子)帶領學員來蘭考實習,創作了《焦裕祿到蘭考》《焦裕祿與老農肖位芬》《焦裕祿帶領除‘三害’調查隊下鄉》等十多幅高水平的油畫,充實到展室內。開館后,焦裕祿展覽館以嶄新的面貌紅火起來,參觀者絡繹不絕。有省內外的、有工農商學兵、新聞記者,還有省、市及中央領導,還有不少國際友人。據統計,來蘭考參觀的國家就有二十多個,曾轟動一時。人們說,在介紹焦裕祿事跡方面,張欽禮是講解最多的一位;在關心焦裕祿展覽館方面,張欽禮是最熱心的一位。張欽禮說:“學習焦裕祿咱要站前頭;實現焦裕祿的遺愿咱要干前頭。”當年“焦展”的工作人員說:“我們最喜歡張書記來了。他往前一站,認真聽我們講解,那是對我們工作多么大的支持啊!再說,他一來,還能及時解決我們辦‘焦展’的實際困難。”然而想不到的是,一九六七年張欽禮蒙冤落難。于是,焦裕祿展覽館被封了館、關了門。焦裕祿的事跡疊遭質疑,宣傳學習焦裕祿的活動頓時冷落下來。一天,張欽禮來到了被搗毀、封閉的焦裕祿紀念館。有人流著淚告訴他:“自從你被關進監獄后,焦裕祿展覽館也被封了門。十來萬冊宣傳介紹焦裕祿事跡的材料、書籍,有的當場燒了,有的送到造紙廠打成了紙漿。因為那上面有你的名字,他們說你是反革命。還因為上面有穆青、周原的名字,他們說穆青是走資派,周原是右派,說焦裕祿長篇大通訊是大毒草……”焦裕祿紀念館被封閉,那么多好的資料、書刊都給毀了,真是造孽啊!張欽禮聽著這令人心酸的訴說,看著被封閉的焦裕祿展覽館,心痛不已。這是他和卓興隆、劉俊生、王保華、程愛云、李國慶等蘭考干部群眾耗盡心血建成的啊!他又邁著沉重的步伐來到焦裕祿墓地,朝著焦裕祿深深鞠了三個躬。望著滿目蒼涼的焦裕祿墓,他哽咽無語。此時,他想起老戰友焦裕祿,想起來蘭考參觀的人們的強烈要求,想起蘭考人民群眾“焦裕祿展覽館不能關閉”“焦裕祿的墓碑太低,碑文太簡短”的呼聲,心中暗下決心:“焦裕祿展覽館一定要盡快修葺一新、重新對外開放!焦裕祿的墓碑一定得重立!”劉俊生回憶說:“一九六七年,周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切接見了張欽禮,張欽禮得以平反復職。張欽禮從北京回到蘭考后,宣傳學習焦裕祿的活動又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焦展’又開了門。張欽禮抽我負責整修焦裕祿革命事跡展覽館。我們除了修復、充實各個展室的內容外,又增加了兩個展室。即前面增加了‘毛主席在蘭考’一室,后邊增加了‘蘭考縣地圖模型’室。”時任焦裕祿展覽館館長扈宗蓮回憶說:“當時蘭考的條件很艱苦,縣委張欽禮、卓興隆、劉俊生對我們‘焦展’的工作很支持。我們講解員介紹焦裕祿事跡,都是滿懷深厚的階級感情,不怕苦、不怕累地宣傳焦裕祿事跡。不論人多、人少,領導還是群眾,我們都認真講解。不少同志嗓子啞了,仍堅持工作。那時來參觀的人特別多,有的是從千里之外來的,我們常常工作在十個小時以上。”她還說:“當時,全國不少單位都想舉辦焦裕祿事跡展覽。為了滿足各地的要求,由劉俊生同志率領走出蘭考,參加舉辦了鄭州‘焦裕祿革命事跡展覽館’,參加了北京‘焦裕祿精神變蘭考’展覽,以及赴京幫阿爾巴尼亞建‘焦裕祿事跡展覽’等工作。人們說,‘焦展’走出了蘭考,辦到了省內外乃至國際上。”政治海洋中的大風大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蘭考就像這汪洋中的一只小船,在風口浪尖上起落。就在“焦展”日益完善、成熟發展之際,一場新的政治災難又向張欽禮襲來。迫害他的人說,張欽禮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是大搞物資刺激、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把他弄到信陽監管軟禁起來。隨著張欽禮再遭磨難,“焦展”再度被關閉,宣傳焦裕祿事跡的大批資料再次被銷毀,焦裕祿的光輝事跡重遭質疑。又是敬愛的周總理搭救了張欽禮,在北京親切接見了他和林縣的楊貴。劫后余生的張欽禮回到蘭考,召開的第一個常委會,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盡快恢復整修焦裕祿事跡展覽館。于是,蘭考“焦展”又重新開館,紅火起來,可謂拜謁如潮,“焦展”又為弘揚焦裕祿精神再立新功。然而,讓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一九七八年,有人借助“揭批查”運動,又以“莫須有”的罪名再次將張欽禮打入大牢。“焦展”又一次被關閉,焦裕祿陵園又一次受冷落,焦裕祿的革命事跡再次遭到新一輪詆毀。知情的蘭考人說,張欽禮的命運和“焦展”的命運是連在一起的。張欽禮平反復職,“焦展”就開門;張欽禮一倒霉,“焦展”就關門。蘭考人民處于對焦裕祿的懷念和對張欽禮命運的同情,仰天長嘆:“這次張欽禮被打入大牢這么多年,誰還能讓‘焦展’再開門?誰還能讓學習焦裕祿的運動深入持久地開展下去啊?”民心即天意,這一天終于來到了。這是歷屆中央領導肯定焦裕祿這一光輝典型并親臨蘭考視察發揮的重大作用,也是新華社的三位老記者穆青、馮健、周原努力的結果。穆青曾對前來采訪的《開封日報》記者說:“學習焦裕祿是人民的心愿。這個心愿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擾。一九八六年我又到蘭考一次。看到焦裕祿墓地荒涼冷落,心里很不是滋味。”見到焦裕祿展覽館被關閉,焦裕祿的親密戰友又遭磨難,很痛心。一九九〇年,穆青、馮健、周原聯袂發表題為《人民呼喚焦裕祿》的文章,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文中一句“千金易求,人心難得,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箴言,也是關系我們黨盛衰興亡的一個大問題”,讓人感悟猶深。【2014年3月17日,習近平參觀焦裕祿同志紀念館,遇到前來參觀學習的河南省中牟縣的黨員干部時說:“我們來是同一個目的,我也是來學習的。”】
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蘭考視察,大力弘揚焦裕祿精神的教導,使學習焦裕祿精神在神州大地再掀新高潮,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在中央、省、地、縣各級領導和蘭考人民的積極努力下,如今“焦展”(現名為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如同一棵幼苗長成了參天大樹。宏偉壯觀的焦裕祿烈士紀念館,面積達兩千一百平方米,坐落于焦裕祿陵園中層(面積為七十三點五畝的焦裕祿陵園,以等高線分為上、中、下三層)。縱觀“焦展”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建設過程,知情人士說:“‘焦展’真是一路風雨,歷經坎坷啊!”還有人感嘆道:“焦裕祿展覽館雄偉壯觀人稱贊,誰知當年‘焦展’創辦人哪!”焦裕祿去世后,最初安葬在鄭州烈士陵園內。當時,在墓穴的北端立了一塊八厘米厚、四十厘米寬、八十厘米高的石碑。上面寫著:焦裕祿同志之墓。沒有生平簡歷。隨著焦裕祿事跡的遠播和學習焦裕祿高潮的興起,在穆青和周原的支持下,河南省委批準了張欽禮、卓興隆等代表蘭考縣委起草的報告,將焦裕祿同志的靈柩由鄭州遷到蘭考安葬,同時追認焦裕祿同志為烈士。當時省民政部門按照有關規定,批準給焦裕祿重新刻了一塊碑,并刻寫了碑文。這個墓碑是青色大理石的,碑高一點二五米,碑文共刻了一百七十四個字。與最初的碑相比,高大可觀了不少。然而,隨著學習焦裕祿活動的深入開展,到蘭考參觀的人越來越多。許多參觀者看到焦裕祿的墓碑這么低,碑文又比較簡單,紛紛提出建議要求,讓蘭考縣委為焦裕祿同志樹立一座高大的墓碑。他們說:如果論級別,毛主席的好學生、縣委書記的好榜樣、黨的好干部就是最高的級別。這種呼聲應和著蘭考人民的心聲,一浪高過一浪。人民的呼聲引起了各級黨組織的重視,但誰能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呢?人們把眼光投向張欽禮,感到非他莫屬。一九六七年,張欽禮將為焦裕祿重新立碑之事,作為宣揚焦裕祿精神的重要工作列入議事日程。他召集有關人員商量研究,形成一致意見后,當即明確卓興隆、楊捍東起草碑文,并向省委寫了請示報告。張欽禮拿著碑文和請示報告,到省委向省委書記劉建勛匯報。劉書記覺得提議很好。隨即叫來紀登奎書記,說:“老紀,你閱批一下這份材料。”紀登奎接過請示報告和碑文,仔細閱讀后,揮筆寫上“同意 紀登奎”五個字。省委領導的支持、批準,讓張欽禮等激動萬分。他們明確縣婦聯主任程愛云負責,由李國慶同志具體經辦,并請來省設計院陳玉林總工程師,按照“凸”字形進行了設計。墓臺由二十五厘米提高到五十二厘米,墓中有二十厘米鋼筋水泥層,墓蓋改為拱形漢白玉,墓碑由一點二五米的青色大理石更換成二點七五米的漢白玉。這塊碑料是經省委秘書長苗化銘批準、鄭州烈士陵園無代價支援的。程愛云、李國慶聞訊十分高興,并迅速帶著解放牌汽車到鄭州把碑料運回蘭考。據當事人李國慶回憶,為了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他曾兩次赴京參觀八寶山革命公墓中的瞿秋白、任弼時墓,又去石家莊參觀華北軍區革命烈士陵園的白求恩墓,還去泰山看過馮玉祥墓……他還精心設計出用四十九塊石料組成“漢白玉石外槨”的焦裕祿烈士陵墓(即碑四塊、墓蓋一塊、閱臺石六塊、壓面石十四塊、斗板石十四塊、土沉石十塊)。為了選擇漢白玉碑的配料,為了選購上等石材砌好墓穴陵槨,程愛云和李國慶可謂嘔心瀝血,千里奔波。李國慶在回憶錄中這樣記述:“我親自去河北曲陽縣西羊坪大理石廠和北京市房山縣尚樂公社石窩大隊選石購料,又親自指揮建成,并在幕后屏風墻上放大制作了毛澤東手跡:‘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張欽禮知人善任。程愛云是戰爭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干部,辦事果斷膽大,不怕艱難困苦。李國慶對焦裕祿是情有獨鐘,任勞任怨,無私奉獻。而且,身懷書法絕技,辦事細心周到。如,他在給焦裕祿陵園選擇石料時,總忘不了揮筆寫下“毛主席的好學生焦裕祿陵園墓碑用料”這樣一行字。此筆一出,人們格外重視。石料廠的人見了這俊逸蒼勁的字,說:“快發,快運!”石料運到火車站,鐵道部門的同志一看,說:“快裝,快轉!”石料運到蘭考,蘭考人見了,說:“快卸,快送!”許多時候,李國慶從外地還未歸來,陵園的石料就到了。人們說:“這就是李國慶速度,是李國慶給石料安上了翅膀。”在修建焦裕祿墓碑的過程中,接連傳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蘭考以“四面紅旗”為代表的人民群眾提出,為焦書記立碑不要政府出錢,由百姓自籌,以表蘭考人民的一點心意。張欽禮被人民群眾對焦書記的情誼和對修建焦裕祿墓碑的支持深深感動。但他不忍心給剛剛從劫難中走出來的群眾再增添一點點負擔,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心意。就在張欽禮、卓興隆、劉俊生等積極協助程愛云、李國慶四處訪購修墓、立碑材料之時,又傳來河北省石家莊市華北烈士陵園的白求恩紀念館無償捐贈漢白玉墓碑石料的好消息。受寵若驚的蘭考人好感動!人心所向,八方支援。張欽禮和他的戰友們代表蘭考人民向省內外給予大力支持的單位、領導和個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在整個修墓立碑的過程中,張欽禮不敢有絲毫的懈怠。請新華社對卓興隆、楊捍東起草的碑文進行了修改敲定;聘請鄭州市著名書法家石蔭亭書寫碑文;從河北省曲陽縣西羊坪請來技術精湛的石匠鐫刻……碑的正面是“焦裕祿烈士之墓”,背面是七百來字的碑文。歷時半年,全部完工。低碑變高碑,墓地煥然一新。

一九六八年三月,給焦裕祿修墓立碑的任務完成了,了卻了張欽禮的一個心愿,了卻了蘭考人民的一個心愿。許多人這樣說:一看到焦裕祿那高大的墓碑和壯觀的墓地,人們就想到為此嘔心瀝血的張欽禮。還有知情人士這樣說:一讀到那飽含著卓興隆、楊捍東心血的碑文,人們就對他們充滿了無限的敬意。當成千上萬的參觀者撫摸著高大的墓碑感嘆焦裕祿的偉大時,有誰會想到宣傳焦裕祿的功臣們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又有誰會想到他們中的許多人會屢遭不幸,晚年竟然過著“三無一有”(即無黨籍、無工作、無工資,有前科)的凄涼日子。真是觀墓撫碑千滴淚,撫今追昔傷透心呀!縱觀蘭考今昔,人們說,張欽禮他們為焦裕祿立了兩通碑:一通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墓碑;一通是感動全國億萬人的心碑!歷史跨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此時的張欽禮已身陷囹圄,他們為焦裕祿立的碑被推倒重刻。什么原因要將省、地委審核批準的墓碑推倒重刻呢?給出的理由是碑文不符合當前形勢。一位到蘭考參觀的上級領導見搭起木架,用電動砂輪打掉原來的碑文時,坦率地說:“碑文是歷史的見證,修改碑文是不尊重歷史的表現。如果要求碑文適應形勢發展,天天修改也跟不上……蠢事!蠢事!”一九八六年,穆青、馮鍵、周原重訪蘭考。見到新刻立的碑,穆青生氣地說:“這讓后人怎么考察,還尊重不尊重歷史……”

二〇〇四年五月,張欽禮帶著無限的眷戀和無盡的惆悵離開了人世。回想起他為宣傳焦裕祿所遭受的種種磨難,蘭考的有識之士揮淚寫下“焦君碑高云天外,駝碑原是屈死魂”的詩句。這功過是非就讓歷史作證、讓人民評說吧!
葉留陽 張占亭:宣傳焦裕祿最早的人——憶張欽禮和豫東沙區造林會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