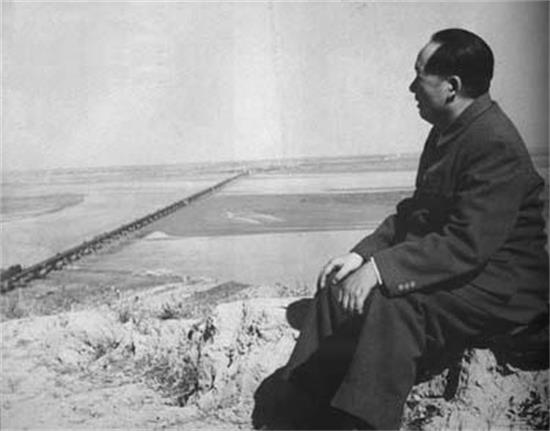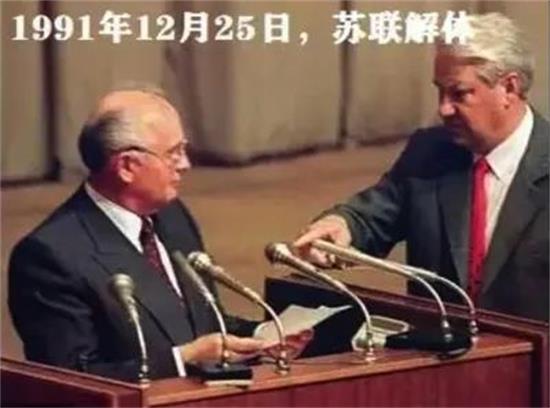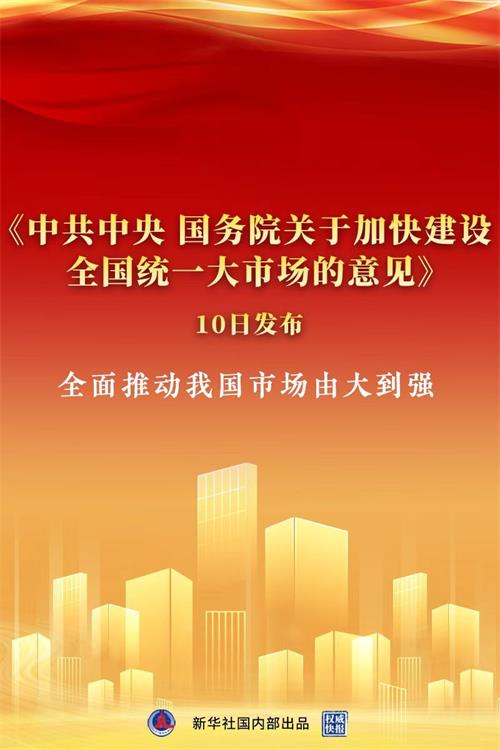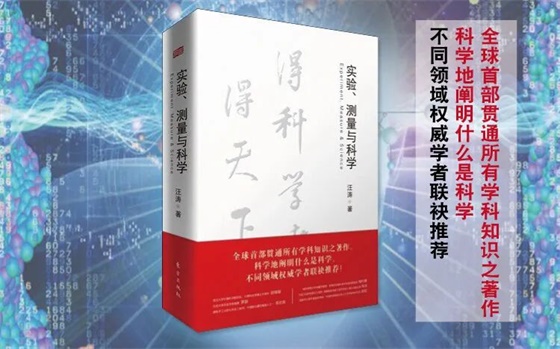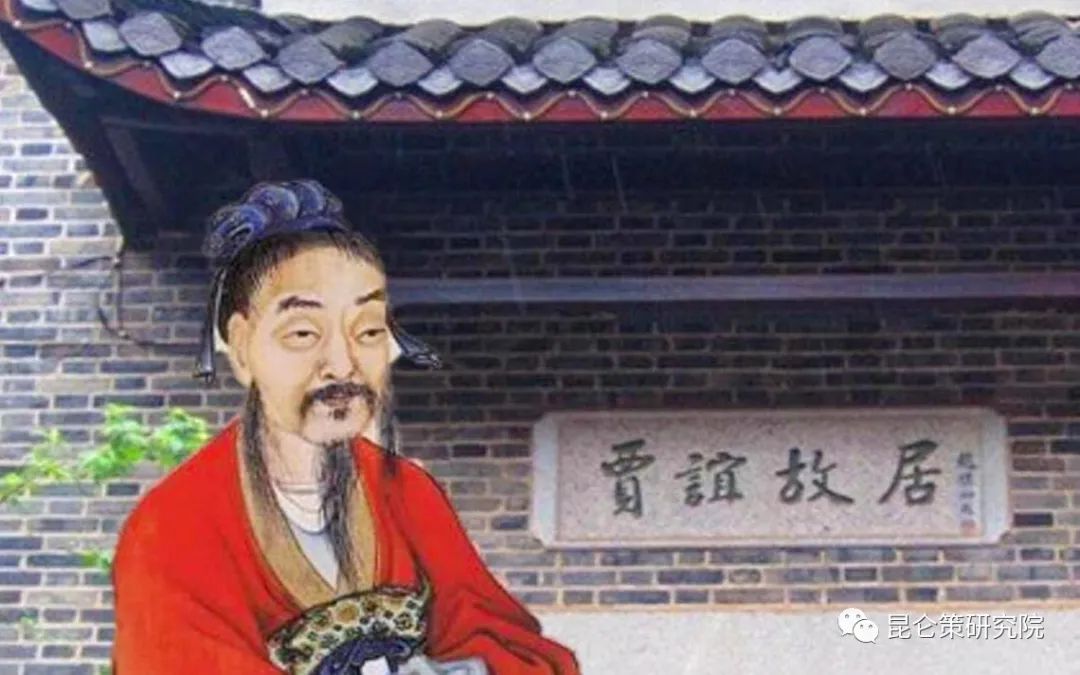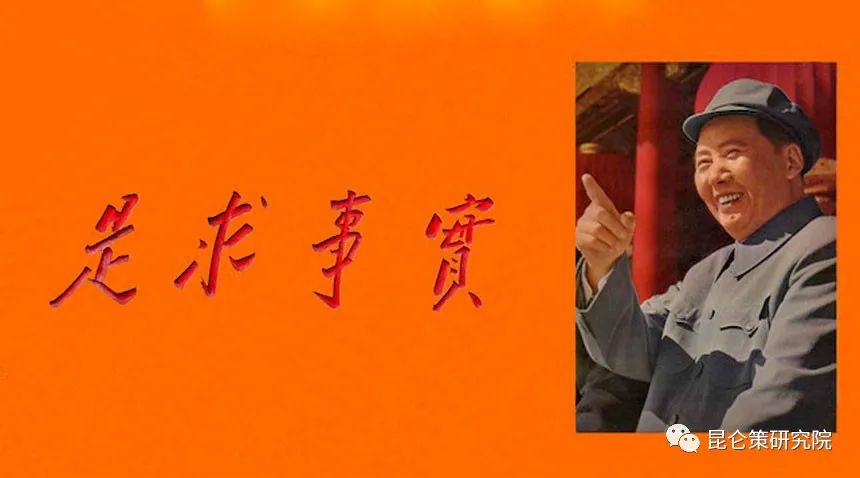我上高中的時候,班上有幾個寧死不屈的搗蛋鬼,他們在課間最愛做的事情,就是趴在教室外走道的欄桿上,看看有沒有本班女生從操場上走過。如果正好看到那種脾氣好的女孩子,他們就會瞅準她的步伐,齊聲大喊:這是一個心理陷阱。因為按照學校體育的規則,學生們應該服從“一、二、一”;但在這個場景里,那個女孩子卻發現自己是在按著一伙“黑幫”的口令行事,下意識的反應就是擺脫他們的節奏。而當她改變步伐的時候,搗蛋男生們則相應調整自己的口令,使她看上去還是按照口令走正步。于是在所有人看來,那個可憐的女孩子活像一個掙不脫操縱線的牽線玩偶,于是爆發出一陣大笑。女生雖然臊得耳紅面赤,卻毫無辦法,只好撒腿就跑,一溜煙逃到教學大樓入口,才算逃過那令人尷尬的魔咒。這種心理陷阱竟然也成為成人世界的最愛,甚至令世界政治精英樂此不疲。最近一個月來,地球上最強大的政治領袖之一,普京,就遇到了這種事情。當他揮師進軍烏克蘭,俄軍戰車才沖入烏克蘭國界,就發現自己猶如身處一個操場上,周圍被無數教學樓包圍,樓道欄桿上趴著無數看客,有很多人在齊聲吶喊:普京顯然沒有預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手機和互聯網把世界變成了一個劇場。他本可以自信而安靜地指揮這場戰爭,但突然有無數觀棋者在他耳邊雷鳴般喋喋不休地品頭論足、出謀劃策。他無疑已經在輿論戰中處于下風:他不僅得承受和平反戰的壓力(停戰),而且還面臨擴大戰爭的壓力(速決)。他失去了戰爭的評判權:他的想法不再重要,這場戰爭已經被塞進看客們“速勝”的評判標準里。于是,他在戰爭的第一個24小時被封了神,第二個24小時卻降為超人,到第三個24小時,很不幸,他的世界形象直接掉了兩格,跨過“巨人”“偉人”層次,“泯然眾人矣”。到今天,專家們談到普京的戰爭時,多半會遺憾地搖搖頭:——“唉,瞧他把事情弄成這樣,換成我也不致如此啊。”
在俄烏戰爭持續了半個月的時候,國內有學者給普京這樣一個差評:“他最初心目中所設想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特別軍事行動’(據說速勝宣傳稿都準備好了,甚至還被誤發出來了),而不是一場生命和政治賭注巨大的曠日持久之戰。他以為這次對烏克蘭的閃電戰,會跟此前的歷次行動一樣,摧枯拉朽,熱刀切黃油,塑造和鞏固他的戰斗領袖的光輝形象。有人分析,這種誤判跟他的信息通道狹窄有關,俄羅斯的高官們似乎都不太敢向他講真話了,都在比著講好聽的話,或者順著他的意思說,從而對他形成了誤導。”
寫得非常形象生動。普京“心目中”啦、“設想”啦、“他以為”啦……儼然作者不僅全天候掌控普京的內心活動,而且隨時俯察著俄國政府大官小吏們的一舉一動。這在超自然領域屬于“讀心術”的法門,在文學領域屬于“上帝視角”的敘事,讓人油然想起烏克蘭女巫界關于用咒語打擊普京的宏偉計劃。這種評價風格至今仍然流行于中外輿論界。如果我們分析俄烏戰爭“速戰速決”論,將會發現存在兩種情況:——一種觀點認為“普京速決計劃失敗”,即普京原本就有一個對烏速決戰的計劃,但沒有料到會遇到烏軍的強烈抵抗;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普京錯過速決機會”,普京本來有贏得對烏速決戰的機會,但被他沒有能夠抓住。
這兩種觀點表面看來相似,但背后的邏輯卻完全相反。第一種觀點的前提是烏軍很強大,無論快攻還是慢熬都奈何不了它;而后一種則認為烏軍很弱小,戰略存在致命破綻,一頓快攻即可打垮它。奇怪的是,同時持有這兩種觀點的論者竟然不在少數。這令人不禁會懷疑很多評論家的觀點并不是自己基于事實和邏輯推論出來的,而是被別人灌輸到腦袋里的:他們只是因為別人對普京喊了“一、二、一”,也就跟著喊起了“一、二、一”,并沒有分析這個口令的是非曲直。所以,“一、二、一”不僅是普京的困境,也是我們旁觀者的困境。俄烏戰爭是智能手機時代的第一場國際戰爭。單純的虛擬產品與復雜的現實問題在液晶屏幕上糾纏在一起,撕裂了我們的常識感,造成了“一、二、一”困境。我們的思維被手機游戲、視頻節目所格式化,趨向于無條件地接受液晶屏幕的催眠,在不知不覺中迎合了別人設置的步調。誰最先為普京喊出了“一、二、一”?首先可以排除的正好是俄國方面,因為俄羅斯官方從來沒有宣揚過“速勝”。然后,可以排除我們國內的評論界。這樣,我們就面對一個有趣的真相:“普京速戰速決”的預言源頭——很抱歉——居然是美國。正是“美國軍事專家”在戰爭打響的時候,搶先拋出了俄軍“96小時拿下基輔”的預言,由是引領了全球輿論的方向。我覺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認真的:早在俄軍發射導彈轟擊烏克蘭之前,美國情報部門就向拜登給出了這一預測,因此拜登就提出了澤連斯基離開基輔甚至烏克蘭的建議。普京不是那種會輕易迎合看客的人。這跟澤連斯基形成鮮明對比。澤連斯基演戲成癖,熱衷于迎合觀眾的想象力,不僅能夠利落地配合“一、二、一”,而且能夠走出各種花式步伐,讓觀眾們興奮不已。他不憚于運用戲劇化的手法引發輿論高潮,在各種媒體上表演“英雄”形象,以此換取旁觀者們狼嗥般的叫好喝彩。
而普京非但不乖乖地順從“一、二、一”,反而一個縱躍,站到操場邊的檢閱臺上,拎起一把寶劍,在手上掂掂,嫌它輕了,于是換了把大砍刀,虎虎生風地舞將起來,似乎要舞上幾天幾夜。這可就超出了鍵盤俠們“一、二、一”的適用范圍。今天,戰爭進行了一個月卻仍然沒有結束跡象,我們事先的很多宏偉構想顯然脫了軌,在現實的墻上撞得七歪八扭。于是,評論界安靜下來了,傻傻地看著普京。他重新又主宰了舞臺。他是務實的政治家,而戰爭是最嚴酷最危險的政治,需要最冷靜最嚴密的現實主義思維。俄羅斯方面對此心知肚明,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指出:美國和歐盟官員試圖通過挖苦俄軍進度不理想,以刺激俄羅斯放手摧毀烏克蘭的主要城市。
可見,這場“一、二、一”游戲原本是預測,最終變成了旨在攪亂普京陣腳的心理游戲。很多本無惡意的旁觀者被集體催眠,變成了美西方的壓力介質。普京由于沒有達到美國預期的目標,而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這一標簽正在而且將繼續引導著很多人對俄烏戰爭的觀感。然而,俄烏戰爭不是一場由網絡投票決定的游戲,普京也沒有義務去完成美國定下的目標。所以,很難說普京輸了,或者看客贏了。最終的結果,很可能是我們發現自己并不瀟灑的旁觀者,而是這場俄烏戰爭的受害者。總有一天,那些對普京表示鄙視的人們將會發現,他們得艱難地理解并痛苦地適應俄烏戰爭所塑造的世界新格局。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曾試圖為普京喊“一、二、一”的人最終卻得按照普京的“一、二、一”行走。
二、被現實層層捆縛的“速勝”幻想
這是一個人類思維方式被電影特技、電子游戲所塑造的時代。很多人沉迷于好萊塢的超級英雄電影中,把屏幕上的事情當作現實,用電影的戲劇化邏輯去理解現實問題。所以不必奇怪,很多人會用戲劇化的思維來分析俄烏戰爭,立足于理想化的基于唯武器論的純粹軍事觀點,要求戰爭主導方實現零傷亡的“速決”。他們相信,由于有無限量地適用于一切場合的先進武器,己方零傷亡的“速決”是不必爭論的結果。不錯,“速勝”是軍事戰略家們的共同理想,早在二千多年前,《孫子兵法》就說了:“兵貴勝而不貴久”。但理想與現實不是一回事。理想一旦照進現實,往往發現現實是錯誤的;在理想中輕松容易的事情,付諸實踐就會處處碰壁、寸步難行。而且政治和軍事也不是一回事:軍事重在“破壞”和“毀滅”,需要短而強的能量輸出;而政治重在“建設”和“穩定”,需要長而柔的能量輸出。普京是政治家,這是他與廣大看客的最大不同。因此,他不可能成為可以追求無限目標的超人。他得在理想目標與現實局限之間尋找平衡,有時不得不犧牲理想主義的最大化成果和最優化路線。按照一些親美人士的想法,他不該發起對烏戰爭,因為和平手段才是最優選擇。但事實上,普京的和平手段已經失效,北約正在跟烏克蘭眉來眼去,美國正著手在哈爾科夫建設“薩德”系統,而無論俄國做了什么,西方的回應都是“制裁”,連普京希望可以保持和改善國際貿易的“北溪”項目也在一波三折之后,被美國扼殺了。當和平手段已經無法逆轉西方持續收緊的絞索,普京如果不想屈膝投降,除了戰爭還能有什么選擇?“本來就該屈膝投降,因為美國是對的!”親美人士會理直氣壯地說。這個問題沒有什么爭論的價值。汪兆銘先生當年就是堅持這樣的和平理想,而果斷投奔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這是個情感取向(“民族大義”)的問題,沒有什么好爭論的。也有人指出,普京低估了烏軍的抵抗意志和戰斗能力,因此輕率地發動了對烏克蘭的閃擊戰。此說誤置了因果關系。要知道,普京對烏開戰的原因不是由于對手的弱小,而是出于時勢的緊迫:俄國已經在烏克蘭問題上陷入絕境,如果不能制止烏克蘭與北約關系的靠近,不能擊滅烏克蘭“收復失地”的計劃,就得面臨長期的地緣政治災難。這是米爾斯海默、基辛格等戰略思想家完全認同的現實。普京必須予以解決,而不能以烏克蘭軍隊戰斗力的強弱而趨避之。
如果普京選擇戰爭是基于時勢的合乎理性的決定,那么,使得普京陷入爭論的關鍵問題就是:普京是否有過“速勝”計劃而沒有能夠實現?或者普京是否有過“速勝”的機會而沒有抓住?
在今天的網絡上,仍然有人在講“普京的速勝計劃失敗”。然而,現在我們并沒有證據表明普京計劃了一場以小時計或者以一星期計的對烏戰爭。他作為一名政治家,固然或多或少得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他也必須明白現實的邊界和理想的限度,設定有限的政治目標;他還要懂得如何確保軍事服務于政治目標,避免暴力的濫用。普京在出手解決烏克蘭問題時,首先必須考慮基于現有的條件設定多大限度的目標,然后再圍繞這個目標劃定軍事行動的形式和范圍,并且確保軍事行動緊緊圍繞政治目的來開展。如果普京有一個速勝計劃,那么這會在俄羅斯政府的言論中反映出來,或者在軍方的行動中顯示出來。但俄政府從來沒有講過任何“速勝”的觀點。即使是俄軍開戰后“勢如破竹”的第一天,在全球國際問題和軍事評論員們興奮地分析俄羅斯該如何用閃電戰打得烏克蘭血流成河、處處廢墟的時候,普京也沒有講過快速結束戰爭,他只是提出了結束戰爭的三項條件。他的意思是清楚的:不達成這三項條件,戰爭就不會結束。顯然,時間并非不重要,但絕非最重要。“速”不是核心,“勝”才是要害。在俄烏戰爭的特定情境中,俄國的“勝”就是實現普京的三項條件,而不是美國方面“替”普京設定的那些無限目標。很多“速勝”論觀點沒有能夠理解這一點,它們模糊地把“勝”界定為占領整個烏克蘭,或者全殲烏軍,或者肉體消滅澤連斯基。這些設想或許都有合理性,但我們只能用普京自己的有限目標(而非美國或其他人的無限目標)去評價其成敗。有必要再次強調,普京的烏克蘭戰爭是一場目標有限的戰爭。他不具備占領整個烏克蘭的資源和條件。他只需要解決最迫切的問題,即烏克蘭中立、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位。但他不可能把戰場局限在頓巴斯,否則當面的烏軍將得到整個烏克蘭(背后是西方)源源不斷的人員和物資補給,使得戰爭無法控制。所以,俄國公開表明是這樣一條戰爭思路:系統性地削弱烏克蘭的戰爭能力,使之在一定時期內無力東顧,保證俄軍專心在烏東作戰。這是短期目標。在烏東戰事結束后,還必須建立一種長期機制,確保被打殘的烏軍不會再次威脅俄羅斯地緣安全,這就是普京關于烏克蘭“非軍事化”“中立化”的構想。普京要通過戰爭使烏克蘭整體性屈服,最好就是烏克蘭的合法政府命令全國武裝力量停止抵抗,在俄羅斯條款的基礎上簽訂的和平協定。這也就意味著俄軍既不需要占領整個烏克蘭,也不需要全殲烏軍,更不需要斬首澤連斯基,只需要運用一定程度的戰爭后果,使得烏克蘭當局喪失戰斗意志即可。所以,我們看到俄軍投入戰斗后,其行動模式并不符合“速決戰”的要求:它嚴格按照傳統陸戰的規范,首先進行火力準備,用遠程火力對敵方軍事設施進行數輪打擊,然后再投入裝甲集團和空降部隊進行突擊。俄軍甚至沒有打擊基輔的烏克蘭中央政府大樓。著名的安東諾夫突襲戰,也只是發生在距離基輔遠達六十多公里的地方。在隨后的一個月中,俄軍步步為營、層層突防、穩扎穩打,這可不是“速戰速決”的架式。必須注意到,俄軍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這一作戰特點,并不是在遭遇所謂“烏軍頑強抵抗”后的被迫采取的B計劃。因此可以斷定,俄軍沒有進行一場閃電戰的計劃。這符合普京的烏克蘭戰略。從去年底以來,他正是采取“保留烏主權,以武促和談”的方式處理烏克蘭問題,戰爭是和平手段用盡后自然而然的選項;而戰爭本身也體現逐步升級的思路,只要某一級軍事壓力產生效果,戰爭就可能中止。我們現在可以指責普京誤判了澤連斯基的戲劇化性格,以為后者會被戰爭的嚴酷性所折服,因此沒有采用雷霆手段、一招致命、快速取勝。但這是事后諸葛亮的思維。事實上,普京并沒有過“速勝”的機會。必須看到,“速決”理想需要無數彈藥來支撐。按照“速勝”論者的設想,先進而無限量的彈藥是保證迅速達成戰略目標的前提。美國的“沙漠風暴”或許體現了這種理想:用炸彈把敵對國家炸平了事,從物理層面消滅反對者和反對票。但那需要很多先進彈藥。美國為了炸平伊拉克和阿富汗,花費了不低于三萬億美元的軍費,外表看似瀟灑而實際上內心痛苦,不僅因為這些錢是以荒廢國內建設為代價的,而且在付出重大代價后并未達到預期的政治目標。普京顯然沒有多得可以隨意使用的彈藥和兵力。他必須精打細算地用好倉庫里的精確制導武器。事實上,即使是美軍,在“沙漠風暴”等行動中,手中的精確制導武器也只夠揮霍半個月,然后就得過一陣緊日子,直到兵工廠完成新的訂單。況且,“斬首”無助于實現政治目標。普京并不需要從肉體上消滅澤連斯基,相反,他需要烏克蘭中央政府存續下去并對戰爭作出理性反應。以肉體消滅為特征的“斬首行動”可能是敗筆,它會導致敵方軍政機構分崩離析,無人能夠控制國家,既不能命令軍隊放下武器,也不能與俄國簽訂具有合法性的和平協議,反而會引發長期的抵抗運動。阿富汗是先例。當年蘇軍對阿明政權實行了極其有效的斬首,結果卻是促成阿富汗抵抗力量的重新組合和加強。普京知道這個教訓。最要緊的是,快速“奪城”“破軍”不具備技術現實性。作為阿富汗戰爭和車臣戰爭的見證者,普京非常清楚城市戰爭和軍事占領將付出巨大的代價。2014年以來,烏克蘭當局在烏東地區苦心經營,已經將頓巴斯變成一個巨型軍營,十余萬軍隊正在集結進攻親俄地區,在預判俄軍將要越境攻擊后,提前化整為零,踞守城市。所以當俄軍裝甲部隊向西突擊時,竟然找不到野外決戰的對象。試問對于這樣的敵軍,如果排除尚處于幻想階段的“機器人化”戰爭,如何能夠“速戰速決”?有人舉出俄格戰爭的例子,但它不同于眼下的俄烏戰爭:當年格軍集中出擊南奧塞梯,為俄軍大規模圍殲創造了條件。在烏克蘭問題上,普京沒有多少選擇余地。他得打這場戰爭,而且不可能寄希望于閃電一擊。面對輿論界“普京速勝失敗”的說法,佩斯科夫指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是一場“有著嚴肅目標的嚴肅行動”,沒有人認為僅需要幾天時間就能完成。他在稍早些時候曾解釋說,“在開始烏克蘭非軍事化行動兩周多以來,俄羅斯軍隊一直在猶豫是否要進入人口稠密的主要城市”。這足以說明制約俄軍行動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對平民傷亡的擔心。我們不該指責普京心慈手軟,歷史將證明戰爭中堅持人道主義立場是完全正確的。俄國對烏戰爭是一場有備之戰。普京應該考慮過開戰后的各種可能,但他不可能等到萬事俱備后才開戰。所以,他現在面臨三大困難:首先,澤連斯基竟然不是一個具有現實感的政客。他顯然不在乎戰爭對國家的破壞,反而陶醉于扮演“民族英雄”乃至“地球英雄”的角色,因此他甚至把自己當作了西方乃至世界的核心,竟然命令聯合國安理會阻止俄羅斯,否則就解散。第二,普京對于西方制裁的歇斯底里程度估計不夠充分。這很難歸咎于他沒有實現“速戰速決”,因為北約在戰前已經考慮了成立烏克蘭流亡政府的可能性,試圖由這個流亡政府操縱一場持久的游擊戰,這就意味著西方原本的計劃就是對俄制裁長期化。第三,普京在西方輿論戰中處于下風。盡管近三十年世界歷史充滿了北約和美國入侵主權國家的記錄,盡管俄國能夠拿出烏克蘭生化武器和人道主義災難的有力證據,西方國家的輿論霸權卻可以宣稱“眼見為不實”,繼續指責俄國“侵略”。在最近的布恰事件中,西方政界和媒體在不聽俄方解釋的情況下,就裁定烏克蘭的故事為實。西方學術界也一個調門地唱衰普京。弗蘭西斯·福山預言:俄軍將突然崩潰,普京將隨之垮臺。乍看起來,普京的處境非常不利。尼爾·弗格森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認為普京將失敗,頭一個理由是俄羅斯永遠不可能在幾周內拿下基輔,趕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這個觀點很重要,它是西方輿論衡量普京成敗的重要指標。然而,正如前述,普京既沒有計劃過占領烏克蘭,也沒有必要趕走澤連斯基。這是“一、二、一”困境的典型事例:評論家們自信喊著“一、二、一”,但普京卻是在耍大刀。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普京失敗”論的真實性。普京的目標小得多:通過戰爭,讓澤連斯基政府采取中立化步驟,接受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既存事實。現在,他的最大難題不是趕走澤連斯基,而是如何才能讓后者坐在烏克蘭總統的寶座上簽署和平協議。很難說普京對俄烏談判抱有期望。澤連斯基在受到戰事逼迫時,會擺出“考慮俄方條件”的姿態,但一旦軍事壓力減輕,他又會回到“寧死不屈”的“民族英雄”套路上。這讓普京很無奈,雖然他現在可以選擇斬首澤連斯基,但同樣無法確保其繼承者有和平的意愿。然而,他還有次優選擇:進一步擴大戰場成果,造成“肢解烏克蘭”的事實,等手上有了盡可能多的籌碼,再來跟澤連斯基們談判和平條件。現在,我們容易忽視的一個因素,是俄烏戰場其實不具備大規模持久戰的前景。烏克蘭不可能奪回戰場主動權。它的戰爭機器已被嚴重摧殘,前線軍民的補給和意志正在耗竭,很難打一場基于“人盾”的持久“游擊戰”。澤連斯基寄希望于北約介入,但北約謹慎地回避了直接介入;它提供了大量武器,但全是適合游擊戰的裝備,不足以令戰局翻盤。俄國國防部已經宣布完成第一階段的作戰任務。西方評論一廂情愿地視為“找臺階下”,而無視其真實的涵義:一方面,俄軍已經嚴重削弱了烏克蘭的戰爭能力,解除了頓巴斯戰斗的后顧之憂;另一方面,神奇消失的基輔方向俄軍退至白俄羅斯,經過重新補給后,既可以再次出擊基輔地區,也可以攻擊兵力不足的烏克蘭西部地區,還可以支援烏克蘭東部戰場。可見,俄軍牢牢把握著戰略主動性。東部的俄聯軍正在緩慢而不可逆地奪取馬里烏波爾,或許還有哈爾科夫。這意味著普京正在完成其戰爭目標的核心部分:完整地奪取頓巴斯地區。現在看來,普京必須考慮澤連斯基拒絕妥協的可能前景。如果他決定擴大戰爭,可以借口“烏克蘭攻擊俄國本土”,從而啟動兵員運用的“國家自衛”條款,動員百萬義務兵、預備役進入戰爭。但更可能的情況是,俄軍不再揮師西進,而是宣布結束特別軍事行動,以較小的成本維持既有戰果。普京手上的資源不足以攻占基輔。前一階段的基輔之戰只是牽制棋,旨在轉移澤連斯基的視線和兵力,使之無睱東顧。現在基輔已經無此價值,不值得付出更大代價。此后,俄軍只需對烏克蘭軍隊集結點、指揮所、大型裝備、交通線進行遠程打擊,即可守住既得成果,令烏克蘭實控區陷于長期低烈度戰斗,使之成為歐洲的巴勒斯坦。彼時,澤連斯基不再會有繼續扮演“民族英雄”的興致,而得認真考慮俄方的停火條件。烏東地區還會有反俄游擊戰,但缺乏穩定補給,也不具備規模和機動能力,將逐步被俄軍及親俄武裝吃掉。普京說過不會肢解烏克蘭,但對于俄軍付出重大代價獲取的戰果,他不太可能輕易放棄。澤連斯基的強烈投機本能正迫使普京更加重視未來和平機制的有效性,確保既得成果不會毀于烏克蘭“收復失地”的沖動。因此,暫時的停火是不可取的,那只意味著給烏克蘭喘息機會然后卷土重來。他將追求一個能夠有效保障烏方不重新武裝并用武力收復失地的長期機制,確保烏克蘭不再構成對俄威脅,并開啟烏東地區“自治化”進程。為此,普京需要設計一套周密的政治和外交戰術,在手中擁有足夠的籌碼的基礎上,用必要而不重要的讓步換來與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緩和。澤連斯基不是普京的對手。如何擊破西方圖謀,才是普京面對的最大難點。基輔當局如果得不到西方的有力支持,就只有投降一途。普京要解決的問題,不僅是戰爭時期西方對烏當局的直接援助(資金和物資)和間接援助(對俄制裁),而且還得應對未來實現停火后西方勢力對俄烏關系的擾動。在短期內,如果普京堅持有限戰爭目標,西方對烏軍援和對俄制裁改變不了戰爭趨勢。在普京完成烏東布局后,就算宣布結束特別軍事行動,也不一定意味著完全停火,而將轉入“以色列vs巴勒斯坦”式的主動防御戰略,即在堅守和建設烏東的同時,對烏克蘭實際控制區重點目標進行遠程打擊。這樣,一方面可以使西方援助的短程防空、反裝甲武器無所措用,另一方面可以使烏克蘭經濟處于持續崩潰狀態,而且迫使西方必須謹慎參與烏克蘭重建。如果出現這樣的狀況,澤連斯基能熬過哪怕區區一年嗎?當然,對于普京來說,這就表示另一個問題:俄國能夠在對烏戰爭降級后,再堅持一年的低烈度沖突嗎?這取決于普京應對西方制裁的能力。顯然,制裁已經對普京形成巨大壓力,但是西方顯然高估了制裁對俄國的殺傷力,低估了對自己的損傷性。弗格森在占卜俄國將如何崩潰時,滿心喜悅地預見到饑餓的俄國人民上街示威。然而,這位曾令我佩服的歷史學者誤置了時空。普京發起的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弗格森竟然不知道:俄羅斯并不缺糧食。實際上,俄國是糧食凈出口國,同時也是化肥和能源輸出國。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實施制裁的西歐國家卻多數得直接或者間接依靠俄國的輸出的初級產品過活。所以,西方制裁的結果不是導致俄國人餓著肚子上街游行,而是自己窗外正在充滿了因為糧食和能源價格飛漲而游行的本國民眾。這樣,事情就變得荒唐了:西方國家在這場制裁游戲中并不是超然而愉快的施害者,而是拳擊臺上試圖打擊對手同時也被打得滿臉鮮血的受害者。曾被我們嘲笑的俄國產業格局成了戰略優勢:它位于源頭和低端,其供給數量和價格將導致全球供應鏈的擾動、震動甚至瓦解。俄國也許會缺麥克當勞,但不會缺面包;也許會缺勞斯萊斯,但不會缺汽油。而一個能夠保障基本生活的經濟體是不可能崩潰的。從戰術來看,西方也極為失策:它本來應該視普京的行動而逐步升級制裁,但它太于過激動,一口氣就用盡了手中的制裁手段。這很尷尬,因為普京只要扛住最初幾波制裁的沖擊,后續的西方制裁力度就會以自由落體狀態下跌。所以,“普京能夠堅持多久”的實質是“西方可以堅持多久”。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在今年年底前顯露崢嶸。普京在合適的時間點上降低戰爭烈度,將給西歐國家下臺階的機會。盡管美國會使出吃奶的力氣推動西歐維持對俄敵意,但它使出吃奶的力氣也無法滿足西歐的能源和糧食需求。歐陸國家很快就將面臨“要普京,還是要饑寒”的痛苦選擇。只要普京在戰爭中獲得足夠多的籌碼,就有足夠的手段引誘西歐國家逐步放棄制裁政策,實現關系緩和。美國也可能考慮直接介入烏克蘭,但其成本代價將高昂得令人無法接受,令其難以作出果斷決策。最近美國的一次民調顯示,近七成民眾不支持冒核戰危險介入烏克蘭。這為普京處理烏克蘭戰爭善后問題提供了窗口期。他將度過困難的上半年,然后把困難的下半年交給西方。丘拜斯的離去,象征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這位改革家有著謎之自信,一直堅信自己當年給俄羅斯開出了正確的藥方,直到俄烏開戰,他終于明白普京早已將他的靈丹妙藥沖進了下水道。在他踽踽離去的身影背后,是三十年來俄羅斯西方化、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失敗后留下的巨大廢墟。曾經是其信徒的普京,現在必須拼盡余生精力,讓俄羅斯從這片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普京以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宣告新俄羅斯——甚至是新世界的誕生。他的備戰時間并不充裕,他選擇的開戰時間亦已十分緊迫。一方面,美國已經著手在烏俄邊境部署薩德等戰略設施,他必須采取斷然行動;另一方面,他必須在2024年大選前消化這場戰爭的后果。他已經遇到過類似情況: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西方的制裁一直沒有完全取消。這一次,他面臨的挑戰要嚴峻得多,兩年的時間更加局促。所以普京已經時不我待地實施其應變計劃。他在3月16日的電視講話體現了今后兩年的施政導向,其效果將決定其政府及政策的連續性。普京是一位精明的戰略家,自然懂得在這次戰爭中付出的成本代價,必須迅速轉變成俄羅斯長期受益的戰略資產,否則他就得黯然離開克里姆林宮。戰爭降級或者結束后,普京很可能通過“重建烏克蘭”計劃,為大俄羅斯區域經濟發展創造新的戰略支點。烏克蘭將在事實上被肢解,第聶伯河以東大片地區成為俄國勢力范圍,頓巴斯地區甚至成為俄國的事實領土。與此相應,原烏克蘭地區人口將依民族情緒和故土情結而重新分布,形成東部俄羅斯化、西部烏克蘭化的格局,使原有的民族對立格局高度強化、深度固化。由于東部工業資源被剝奪,新烏克蘭的經濟發展面臨更多問題。即使俄烏實現完全和平,“美英主導的烏克蘭馬歇爾計劃”也不太可能實現,因為美英拿不出這筆巨額資金,而且這將不必要地加劇歐洲國家間競爭,也得不到歐陸國家的熱情支持。但烏克蘭東部地區將在俄羅斯主導下推進戰后重建和新工業化進程。該地區屬于沙俄—蘇聯工業的核心區,其再工業化進程有利于俄羅斯、白俄羅斯的產業深度整合。很多人猜測普京可能會建立一個“小蘇聯”,但目前這只可能在歐洲區域發生,事實上是小斯拉夫經濟一體化。長遠來看,如果斯拉夫核心區域經濟成長取得實質性進展,原蘇聯的諸中亞加盟共和國很可能參與進來。中亞國家雖然有靠向西方的意愿,但它們在蘇聯解體后三十多年時并沒有被西方陣營所接納,反而被一再施加顏色革命的圖謀,客觀上存在“抱團”求生存圖發展的動力,最終可能形成以俄羅斯為核心、以集安組織為框架、加上東烏地區組成的經濟共同體。重構斯拉夫核心區經濟體系,這需要一個通盤的考慮。國際環境的急劇惡化,將迫使普京跳出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范式,收縮和優化全球化和市場化戰略。從普京3月16日的講話來看,可以預見俄羅斯將加強政府的主導性,更加主動地用國家戰略引導經濟發展,對內發揮科技優勢、提振工業經濟、挖掘資源潛力,力求重塑足夠強大的經濟動能;對外則減少對西方依賴、推動進口替代,補足由于西方公司撤離而形成的產業和產品空白,以戰略性產品輸出推動國際關系的重構。這其實就是一個強化國內和區域的“內循環”鏈條的前景。這不僅為俄國本土企業,也為其友好國家的企業創造了新的機會。面對普京的挑戰,美國的應對策略顯然缺乏遠見的,它既沒有深入研究遠景目標,也沒有仔細分析制裁措施的后果。一開始,它似乎是要準備一場新冷戰,但采取的措施卻與事態的核心問題不相匹配。在冷戰時代成長起來的美國官僚們沒有意識到,俄烏沖突只是區域性的民族紛爭,根本不是足以把全球分成兩個陣營的意識形態對立。除非美國親自下場助戰,否則俄烏戰事既不能可持續也不可能激化。隨著戰事冷卻,盟友們的戰斗熱情必然持續消退,美國將發現“反俄陣線”將成為自己的尷尬獨舞。由于在俄烏戰爭中偷奸耍滑,美國作為“世界領袖”的形象已經破損。表面上,美國實現了北約的團結,但在骨子里,西方國家集體陷入了急性抑郁,一方面是政治亢奮,另一方面是經濟焦慮。反俄同盟現在的一致和堅定只是暫時的激昂,它們內部的虛弱和分歧才是深刻影響未來的動力。不錯,美國因賣出大量軍火而得到商業紅利,但卻犧牲了歐陸盟國的經濟利益。今天的美國已經迥然有異于“柏林危機”時代的美國,不再具有牽引歷史的實力;它把既無能又缺德的烏克蘭政權樹為道德楷模,實質上挖斷了所謂“普世”價值的根子;它草率地阻斷美元交易渠道,凍結外國公私資產,自我污毀了“資本天堂”的金字招牌。如果俄烏戰爭降溫或者和解,美國將面臨全球控制力弱化和西方陣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雖然不會與西方體系“脫鉤”,但會有相當大一部分經貿往來會獨立成篇,從而削弱和約束對美國至關重要的美元霸權,使美國更難應對國內經濟衰退;另一方面,美西方各國脫離便宜的俄國能源、礦物和農業產品,必然推高經濟運行成本,而同時友俄諸國卻擁有相對低廉的能源和原料來源,導致美西集團在世界經濟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加速西方影響力的持續衰落。這迫使反俄陣營中的歐陸各國在意識形態的高調與經濟利益的現實之間作出選擇,如果它們決定優先解決陷入麻煩的國內經濟,而不是強令正在老齡化的社會去組織新的十字軍,美國陣營的政治“共價鍵”就會破裂。不言而喻,普京將不失時機地以經濟利益為誘餌,離間歐洲大陸與美英的關系,重新構造歐洲經濟格局。因此,美國繼1980年代喪失商品霸權后,又在2020年代自廢美元霸權,其全球經濟影響力已然衰退。離開了經濟后盾,武運也難長久。未來一個時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尚處于美國陰影下,普京還沒有真正撞垮這道墻。階段性成果尚需時日。但如果不發生核戰,世界必然走向經濟多極化、政治多元化的新秩序。我們如何稱呼這個新的時代?“后西方時代”還是“新冷戰時代”?我覺得“后歷史時代可能”更形象。因為福山已經宣告了歷史的終結。當布林肯逼迫世界各國與美國一道站在歷史那邊時,我們不需要去追隨已然終結的歷史,而是站在充滿變數和機會的未來一邊。(作者系政策和戰略研究者;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m.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