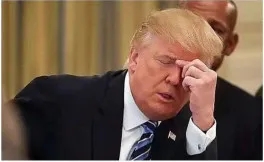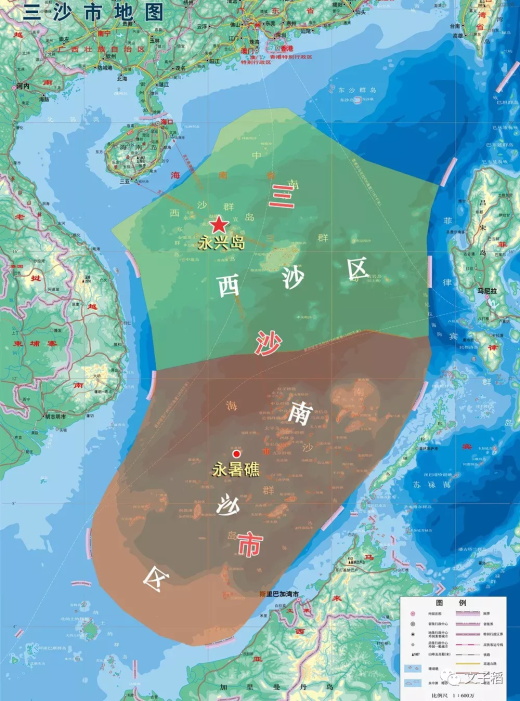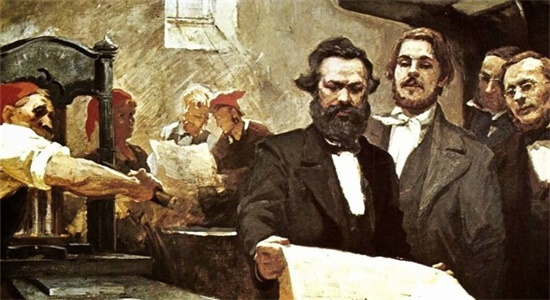1922年1月21日,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終于在一件不很寬敞的會議廳中開幕了。……開會后幾天的一個晚上,施瑪斯基偕同共產國際一位英文翻譯愛芬(此人后來任斯大林秘書),邀請張秋白[1],鄧培[2]和我三位中國代表以及朝鮮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宮。經過兩次衛兵崗位的查詢,由施瑪斯基出示通行證件,向之說明來意后,我們的車子就停在了一座辦公大廈的門口。約九點鐘時,我們被引到一個小客廳里,施瑪斯基這才說明此來是應列寧的約見。
須臾,列寧就從隔壁的辦公室過來接待。他出現時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經過施瑪斯基的一番介紹之后,談話便在輕松的氣氛中進行。
張秋白首先要列寧對中國革命做一指教,列寧很直率的表示,他對中國的情況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了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他轉而詢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并未多加說明即作肯定表示: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寧旋即以同樣的問題問我,并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我簡單的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列寧對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滿意,并沒有繼續問下去。
接著他又詢問金奎植有關朝鮮革命運動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語比我們說的較為流利,做了一番相當詳細的陳述。列寧也對他表示一番鼓勵。繼之,列寧與施瑪斯基用俄語交談;我們從旁邊觀察,看出他們的情態十分親切。據我所知施瑪斯基還是在1905年以前見過列寧,此后就再沒有會過面了。此次相逢,他們暢談著別后的境況,以及西伯利亞遠東一帶的和這次大會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瑪斯基對他的領袖極其尊敬,但也極其自然;而列寧對施瑪斯基似也充分流露著友愛神情。這種親密的同志關系,在列寧逝世以后的俄國,再也不易發現了。
那時列寧似患重聽,也許由于我們的英語說得太壞,更是他難以聽懂。他在談話時,總是傾斜著頭向發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滿自信的光芒,全神貫注,一個字也不肯輕易放過。愛芬的翻譯如果有一個字不甚恰當,它就和氣地加以點名;如果我們說話的意思不夠清楚,他也要問個明白,看來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辭的時候,列寧以親切的態度雙手緊握著鄧培的手,用英語向我說:“鐵路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在俄國的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請你將我的意思說給他聽。”鄧培這個樸實的工人領袖,聽了我的翻譯后張口大笑,點頭不已,作為對列寧盛意的回答。列寧賭此,也露出樂不可知的笑容。
這次談話因為翻譯的費時,花去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談話的內容卻很簡單。我們一行4人對于這次晤談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談時那種友愛親切的氣氛,使大家事后稱道不已。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純正的教主。我從未在其他的蘇俄領袖身上看見過和列寧同樣的品格,好像他們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氣、俄國味之類。
東方出版社出版說明:

歷史上,一個人在人生生涯中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并不鮮見。
汪精衛從謀刺清攝政王載灃的革命黨勇士到大漢奸,滿清四品高官楊度后推舉袁世凱稱帝,最終加入共產黨等,張國燾則從中共的創始人到國民黨軍統特務再到加拿大寓公。
各有各的人生悲喜劇。
但張國燾的悲劇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曾經耳熟能詳、高度警覺而后來卻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種思想弊病。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建黨初期的高級領導人。在長期生涯中,從極“左”到極右有其不光彩的軌跡。無論在黨的三大上,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離開核心領導層,還是在鄂豫皖蘇區大開殺戒,以AB團的名義屠殺大批共產黨人。其極“左”達到登峰造極。

此處和附近的沙子崗、潘灣山洼是“大肅反”屠殺紅軍的地方。紫虬攝于2016.2.20,白雀園東門外河灘
在1931年8-11月期間,發生了“白雀園大肅反”。
1931年4月,從蘇聯回國不久的張國燾和陳昌浩,由顧順章叛變前送到武漢,再往鄂豫皖蘇區,成立以張為首的鄂豫皖中央分局。
作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推行的王明左傾冒險路線脫離實際,受到蘇區紅四軍高級將領的抵制,許繼慎和曾中生、徐向前等9月4日在英山雞鳴河會議上聯名向分局和中央寫信,反對張的決策。同時,“空降”到鄂豫皖的張國燾在黨內殘酷斗爭,結合個人野心開始了瘋狂的奪權鎮壓分裂活動。
10月上旬,驍勇善戰的紅四軍移駐河南省光山白雀園地區。張國燾便從新集專程趕到白雀園,主持“全力來肅清四軍中之反革命及整頓四軍”的白雀園“大肅反”。[3]恰在此前后,國民黨的離間計也發揮了作用。
1937年4月,時任國民黨江蘇省政府委員、江南行署主任兼江南挺進第二縱隊司令的冷欣,在與我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同志會面時,曾洋洋得意地說:"我們在鄂豫皖略施小計,你們便殺了許繼慎”。[4]
張國燾在白雀園火神廟審訊中,“對許繼慎、周維炯、姜鏡堂、陳奇、李榮桂、曹大駿等高級干部,(其中大部分是鄂豫皖創建根據地的創始人、參加者,戰功卓著)采取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對他們進行吊打、踩杠、烙鐵烙、坐老虎凳、十指竹釘、煙熏鼻孔、倒灌辣椒水、赤腳站燒紅的磚頭等等。[5]張國濤本人是北大的學生領袖,但對紅軍中的知識分子采取了絕對的排斥態度,認為知識分子最危險,采取了一概斃殺的決絕態度。

右半邊長列小字,是被害團職以上烈士名單。紫虬攝于2016.2.20百雀園香爐山頂
徐向前元帥回憶,張國燾捕殺人,“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殺人不講證據,全憑口供”。“陳昌浩同志就更兇嘍,捕殺高級干部,有時連口供都不要。這個人干勁十足,但容易狂熱。”[6]
張國燾等人極左掩飾下的罪惡行為,得到以秦邦憲(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的支持。“中央完全同意關于反對四軍領導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確路線的決議”,“關于肅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須堅決的進行。在進行中必須根據階級的立場,分別首從。嚴厲的處置首領...”[7]
經過白雀園開始的“大肅反”,紅4軍4個師12個團的團級以上干部只剩下王樹生、倪志亮兩個人,有的團、營以上干部換過3次,排、班干部大部分換過兩三次,有的換過4次。[8]
1931年11月22日,陳昌浩在鄂豫皖蘇區彭楊軍事政治學校作《關于此次肅反詳情之報告》中說:這次肅清改逆1000人,富農及一切不好分子一千五六百人。作為反革命被殺的,僅在紅4軍中,就“有兩個師長許繼慎、周維炯,1個師政治委員(龐永俊),8個團長,5個團政治委員..."

先烈們長眠地下,英靈注視著白露河兩岸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日新月異。紫虬攝于2016.2.20香爐山上
有些吹捧張國燾的人,吹噓張對紅四方面軍的控制能力,不過是美化白雀園“肅反”的政治打擊、屠殺等極左手段罷了。
張國燾的極左,既是其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唯我獨革、唯我獨尊的政治野心表現;到了革命受到挫折的時候,就變成了右傾逃跑主義。
1935年6月,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后,在研究前進方向的懋功會議上,即使按張國燾自己的回憶,其提出的前進的三個方案,中心還是西進。以后,無論南下,還是西路軍西渡黃河迫使中央承認即成事實,指導思想的深處,都是畏敵避戰的思想。至于軍力脅迫中央,另立“中央”,直到1938年4月,只身投入蔣介石懷抱,委身為軍統特務,徹底走向反面。
叛徒結局,既是其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必然軌跡,在思想方法上,則是對革命徹底失望,對其前半生的試圖以革命生涯謀取個人目地的萬念俱灰。
1968年10月21日,三名美方人員(兩名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官員和一名美國專家,為首的是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領事館官員米西蘭尼奧斯)對張國燾進行專訪,在這次訪問中,張國燾大談他對“文革”走向的判斷,在張國燾看來,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絕不僅僅是(如外界所推測的)出于政治權力的考慮,他認為毛澤東此舉還有著哲學上的思考。在分析毛澤東的特點時,張國燾認為毛有著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認為作為一個農民社會主義者,毛澤東有一種對“平等”的渴望,一旦他發現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提供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趨勢時(也就是所謂的“變修”時),毛便想采取措施來達到目的。這是“文革”發動的一個重要原因。[9]
這是張國燾在1949年不堪忍受國民黨內部的傾軋,在香港、美國做了近20年寓公的反思。
從其曲折的一生看,到了生命的晚年,從共產黨領導人到叛徒,也算“執兩端而竭焉”,人在寥落晚年,偌大的世界,眾叛親離,遭人鄙視,煢煢孑立之際,算是難得的清醒。這種清醒,不過是常見的在人生晚年或逆境中相對客觀、超脫一些,對于其人,極為難得,但和政治信仰無關。
在回憶錄中,張國濤把列寧稱作“教主”,在對列寧個人的褒贊崇敬中,流露出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鄙夷。
那么,前文所說,張國燾的悲劇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曾經耳熟能詳、高度警覺而后來卻似乎麻木、淡忘的一種思想弊病是什么呢?
這個思想病根,就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指出的: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王明先是“左”傾教條主義,照搬蘇聯,丟失90%蘇區,黨內殘酷斗爭;以后又轉向右傾,一切經過蔣介石領導的統一戰線,造成皖南事變損失。
這種思想方法上的“左”右搖擺,主客觀分離,在建國后,也表現在各個時期,如五十年代,一再違背八屆三中全會對反右斗爭的估計,違背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毛主席組織制定的畝產分別400、500和800斤的糧食《綱要》,先是反右擴大化,直至誘發浮夸風、放衛星、共產風,餓死人;四清時割資本主義尾巴,六十年代中期派工作組反右,形成形“左”實右。改革開放后,思維方式采取社資折中主義和實用主義,違背對立統一法則,宣揚市場經濟“中性論”、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混淆社會主義本質和根本任務等,長期干擾深化改革開放。
革命時期和建國以來“左”右搖擺思想認識路線上的病灶,就是主客觀分離,脫離群眾路線。例如社資二元論基礎上的折中主義,往往是歷史唯心史觀的表現;而實用主義,則形式上有機械唯物論的傾向,實質上依然是有用即真理,最終陷入唯心主義。
看清了這個歷史,也就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如同人行走,總要重心隨步伐左右輪替,但搖擺大了,就要失去重心,帶來損失。因此,時刻警惕脫離人民群眾,時刻警惕英雄史觀,時刻把握習近平總結的“為了誰,依靠誰”這個根本問題,保持實踐和認識的統一,主觀和客觀的統一,這比堅定的聲明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要困難的多。
毛主席的弟媳,革命老人朱旦華曾經說過,如果張國濤不叛變,毛主席也會把他留在中央。這是完全可能的。正如在七大、八大上毛主席曾經給許多同志做工作,把王明留在中央委員會。毛主席的意圖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不管犯了什么錯誤,只要他愿意做自我批評,就依然是自己的同志。至于他們的忽“左”忽右,完全可以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吸收教訓,教育其他人。
歷史證明,有些人,改也難。有些在黨內仍有地位的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名號,但思想方法上,或者教條主義,或者實用主義,或者折中主義,或者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上共同的特征,就是脫離群眾路線的唯心史觀,以主客觀分離,認識和實踐相脫離。如七屆、八屆中央委員王明,至死歪曲歷史,攻擊中國和黨的領袖,倒還不如臭名遠揚的叛徒張國燾晚年在某些問題上來的清醒。
2020年4月26日
注 釋:
[1]張秋白,早年曾參加中國同盟會,后來成為國民黨趨炎附勢政客,1928年死于幫派暗殺。
[2]鄧培(1883—1927),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的黨員,中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和著名活動家。他的一生,為中國的革命事業,特別是早期的鐵路工人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1927年4月,在廣州四一五反革命政變中,被新軍閥逮捕,在獄中遭到嚴刑拷打,堅貞不屈。6月22日,在廣州從容就義。
[3]《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鄂豫皖時期·下),解放軍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頁。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58頁。
[5]《中共黨史資料通訊》1982,第280頁。
[6]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160、161頁。
[7]《中央給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
[8]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第140頁。
[9]中青在線特約撰稿:黃東,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
(來源:昆侖策網,原載“紫虬視野”微信公號【作者授權】,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m.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紫虬|讀張國燾覲見列寧的回憶,看極“左”到極右軌跡的思想特征
2020-05-06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北進期間,張國燾曾擬經果洛三大部落西渡黃河
2020-04-26?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蕭光畔:以“絲綢之路”為契機,打造中國西進大戰略
蕭光畔:以“絲綢之路”為契機,打造中國西進大戰略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