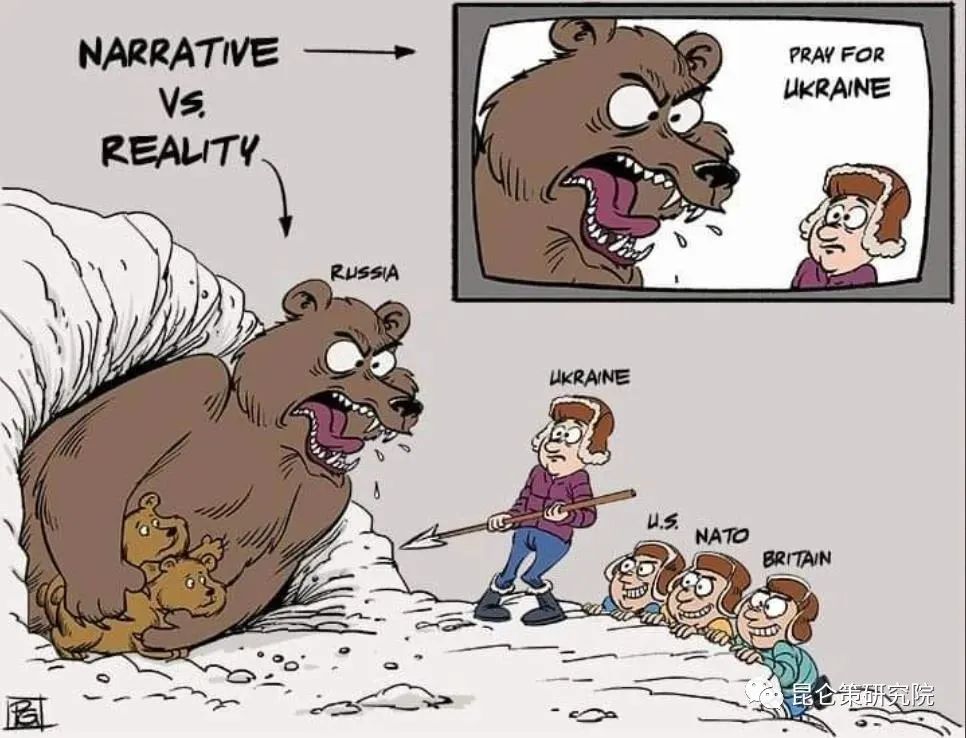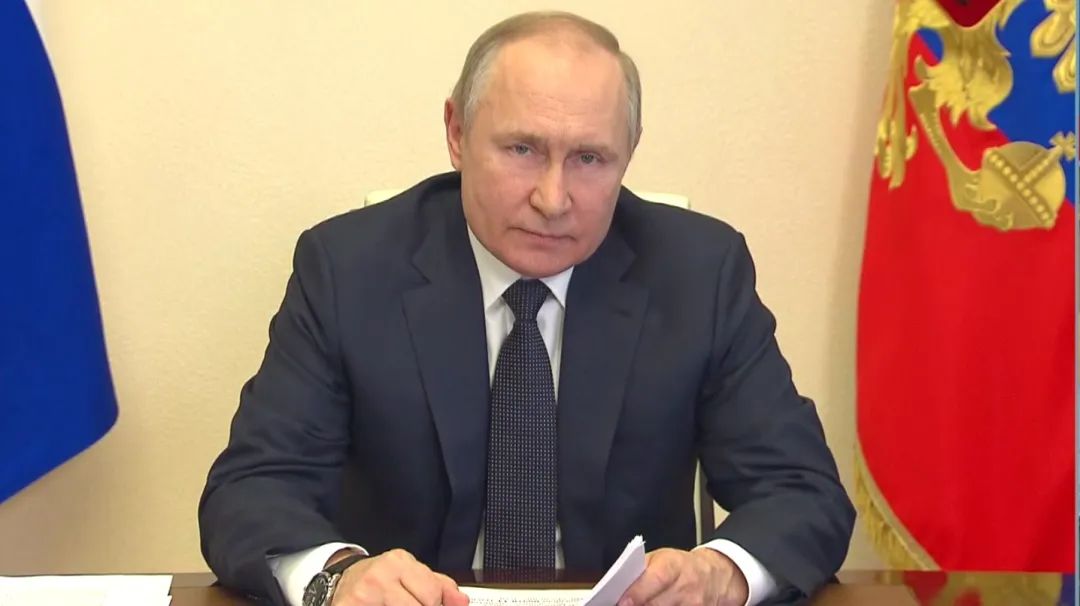評姚洋教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中華文明的建構》
【提要】針對姚洋教授和公方彬教授的觀點,文章指出:(1)經典馬克思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流。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系,這個關系必須明確,必須擺正。(2)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必然產物,反過來又指導并引領著馬克思主義實踐,二者不可割裂。(3)我們之所以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是因為我們必須正確引導、促進符合現階段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系健康發展,而并不是說私人資本從此就不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了。(4)馬克思從來沒有簡單地、片面地、孤立地斷言“赤貧多的原因源自剝削”,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去揭示貧窮的根源。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疊加態中,來看待并解決貧窮問題的。
最近讀了姚洋先生寫的文章:《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現代中華文明的建構》。姚先生的這篇文章,《文化縱橫》公眾號以《姚洋最新萬字方案: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挑戰與政治哲學的重構》為題,專門做了隆重推薦。姚先生最終的結論是:
“黨在理論層面的中國化,必須從吸收儒家政治哲學開始。馬克思主義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資本主義的產物,傳入中國之后,成為黨戰勝舊制度及其一切從屬勢力的武器,也為黨改造中國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原始形態不適合作為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指導,我們要做的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此外,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中華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據一席之地,就必須向世界展示自己獨創的文化。如何在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前提下構建黨的新理論,是黨在百年華誕之際最重要的任務。一個可能的取向是,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繼承前者而揚棄后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點與中國的務實主義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處。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核心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在資本主義早期,生產相對簡單,資本與勞動的分野比較明確;但在當今全球化的生產和交換格局之下,資本和勞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分配被證明是較有效的社會分配機制。中國的實踐也表明,建立按要素分配的市場機制,是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以儒家政治為體,重構黨的理論體系,是黨完成回歸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關鍵一步。”
對于姚先生的結論,我是不同意的。坦率地講,每當讀到明顯有違基本常識和基本邏輯的文章——且這些文章的影響力又非同一般——我就會有“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覺。眾所周知,“和諧相處”以及“和稀泥”是晚近以來學界交流的潛規則。要不要將我點評姚先生的看法公布出來,我有些猶豫。然而,卡在喉嚨里的魚刺,不吐出來不行。本著堅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原則,我決定把“魚刺”吐出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姚先生認為:“當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大挑戰,是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張力。”何謂“張力”?在物理學中,“張力”的意思就是指彈性物體被拉扯時所產生的應力。在哲學中,“張力”的意思就是矛盾或抵牾。姚先生關于中共面臨挑戰的這個看法,我是贊同的。眾所周知,“實踐與理論之間的張力”,的確是“當前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一大挑戰”。那么,姚先生認為應當怎么解決這個“挑戰”呢?姚先生提出:“從儒家學說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是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姚先生提出“從儒家學說出發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倒也不失為一種解決方案。至于這方案是否“可行”,那還得看方案的內容是否實現了姚先生在文中提出的重要任務。那么,姚先生提出的重要任務是什么呢?姚先生強調:“如何在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前提下構建黨的新理論,是黨在百年華誕之際最重要的任務。”按照通常的解讀,“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是守正,“構建黨的新理論”是創新。守正是創新的本源,創新是守正的開拓和深化。中國共產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守正與創新”的任務不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艱巨。然而我必須強調的是,創新首先要繼承。拒絕繼承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理論創新,只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何來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換言之,經典馬克思主義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流。二者是“源與流”的關系,這個關系必須明確,必須擺正。因此,姚先生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始形態不適合作為黨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指導”,顯然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的新理論的出發點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落腳點也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觀照下的中國國情。也就是說,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以及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我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人沒有做過的,對于中國共產黨第二個100年的偉大目標,我們充滿信心。但是,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必須而且能夠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邏輯來加以回答和解讀,對此,我們也應該充滿信心。如果我們的理論解讀與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以及基本觀點和基本立場南轅北轍,背道而馳,那么這樣的“新理論”是否真正創新了馬克思主義,就很值得懷疑。遺憾的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存在著“羞于繼承”,甚至是“不屑于繼承”的現象。由此可見,姚先生所說“如何在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前提下構建黨的新理論”,其要害并不在于“新理論”是否足夠新,而是在于“新理論”是否真的“保持了馬克思主義精髓”。要回答這個要害問題,那就得看“新理論”究竟“新”在哪里。下面,我們來看看姚先生是怎樣“構建黨的理論”的。那么,姚先生是怎樣“構建黨的理論”的呢?姚先生說:“一個可能的取向是,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繼承前者而揚棄后者。”請大家注意,姚先生的“新理論”新就新在:必須“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讓二者一刀兩斷。“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實踐”一刀兩斷之后,又將如何呢?對此姚先生提出了:“繼承馬克思主義哲學,揚棄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取向。姚先生的這個“取向”雖然只是“可能”,但卻很奇特。我請問姚先生:“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能一刀兩斷嗎?能切割開來嗎?我打個比方,姚先生的這個“取向”是:將馬克思主義的頭顱與馬克思主義的身體一刀兩斷。也就是說,姚先生只要馬克思主義的頭顱,不要馬克思主義的身體。只要馬克思主義的頭顱,這是什么奇葩?不要馬克思主義的身軀,這是什么邏輯?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頭顱(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簡稱“馬哲”),姚先生把它與儒家做了一個很親熱的比較:“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點與中國的務實主義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處。”在我看來,要在馬哲與儒家學說里面找到“相通之處”,大概并不是什么難事;應當汲取儒家學說中的精華,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題中之義。但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家學說有沒有“相通之處”,而是在于二者有沒有“本質區別”。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家學說的區別,并不僅是現象或幾何形狀的區別,而是有本質上的區別。在有人強勢呼吁“馬克思主義應當與儒家學說稱兄道弟”的語境下,澄清二者不是“同一戰壕的戰友”,我以為十分必要。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家學說的本質區別或存在于方方面面,比如,在本體論、歷史觀、價值觀等等方面,二者都存在著本質區別。就歷史觀而言,二者的本質區別在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邏輯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儒家的中庸思想則信奉的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同志們想一想,只講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儒家學說的“相通之處”,回避甚至抹殺二者的“本質區別”,這樣一路“相通”下去,姚先生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還能有“相通之處”嗎?那么,姚先生為什么要“揚棄馬克思主義實踐”呢?姚洋給出的理由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核心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在資本主義早期,生產相對簡單,資本與勞動的分野比較明確;但在當今全球化的生產和交換格局之下,資本和勞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分配被證明是較有效的社會分配機制。中國的實踐也表明,建立按要素分配的市場機制,是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眾所周知,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大理論基石,若把這兩個基石搬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無從立足了。倘若姚先生真的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已經過時,那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應下課,從此讓“要素價值論”和“按要素分配論”取而代之。但問題是,姚先生用“資本與勞動早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來證明“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剝削理論”已經過時,用“當下的社會分配機制”來證明“要素價值論”的科學性。如此“存在即合理”或“存在即科學”的證明“秘訣”,我認為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同志的話,對于如何繼承,繼承什么,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按照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邏輯,同理,當代中國經濟學“新理論”的根本也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馬克思已經科學地證明,只要商品、貨幣、市場經濟還存在,勞動價值論就不會過時。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剩余價值論依然沒有過時。因此,若要“構造黨的新理論”,必須堅決捍衛和繼承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否則,再時髦的“新理論”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此外,商品拜物教理論、資本積累理論、再生產理論、兩大部類理論、利潤平均化理論、地租理論等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充滿著豐富的科學思想,我們為什么不能繼承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隨著時代的發展、實踐的深化,當然要不斷發展,并且也會加入中國元素和時代元素,甚至也不拒絕對西方現代經濟學中具有科學成分的理論和工具加以借鑒。但是不論怎么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能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政治經濟學,發展著的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必須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基本觀點的政治經濟學。在“揚棄馬克思主義實踐”之后,姚洋先生信心滿滿地說:“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以儒家政治為體,重構黨的理論體系,是黨完成回歸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關鍵一步。”姚先生的“關鍵一步”的“關鍵”,說白了,就是要“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并且是“繼承前者而揚棄后者”。
馬克思主義哲學(簡稱“馬哲”),就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即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馬克思主義實踐(簡稱“馬實踐”),就是基于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千萬不要忘記,“馬實踐”既包括發展生產力的實踐活動,更包括基于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生產關系革命——階級斗爭不過是生產關系革命的題中之義罷了。
這里順便指出,“階級”和“階級分析”并不是馬克思的“發明”,而是客觀存在的鐵一般的事實。有關“階級”和“階級分析”的理論,馬克思并不擁有“專利權”,這是常識。早在馬克思之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梯葉里、基佐、米涅等人就認為,階級斗爭是理解近代歐洲革命的鑰匙。在這些資產階級學者的眼里,17世紀的英國革命、18世紀的法國革命,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同封建貴族、僧侶的階級斗爭史。至于斯密、李嘉圖,這兩位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公開承認階級的存在并做過階級分析,那更是經濟學的常識。當然,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并不是跟在資產階級學者的屁股后面“照著說”。馬克思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有三個亮點:(1)馬克思把階級看作歷史范疇,即“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馬克思指出了階級斗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在關系,即“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馬克思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地位,即“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問題在于,“馬哲”既是“馬實踐”的必然產物,反過來又指導并引領著“馬實踐”。一言以蔽之,“馬哲”與“馬實踐”不可割裂!這里的邏輯很清楚:若拋棄了“馬實踐”(姚洋的主張其實就是要拋棄“馬實踐”),也就從實證的角度否定了“馬哲”;若真要繼承“馬哲”,那就必須而且必然發揚光大“馬實踐”。姚洋的方案之所以吊詭,就在于:他既要繼承“馬哲”,又要拋棄“馬實踐”。這就如同魯迅所說:“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真是難為他了。按照姚洋的定位,“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言外之意,否定“馬實踐”,理所當然地就要否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然而,“馬哲”的科學性質,是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得到證明和檢驗的。換言之,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實證性質,必須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能得以貫徹和呈現。對于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列寧說:“社會學中這種唯物主義思想本身已經是天才的思想。當然,這在那時暫且還只是一個假設,但是,是一個第一次使人們有可能以嚴格的科學態度對待歷史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假設。”既然唯物史觀“還只是一個假設”,那么它就需要實證檢驗(證實或者證偽)。那么,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如何被實證檢驗的呢?對于唯物史觀的實證檢驗,列寧給出了如下說明:“馬克思在40年代提出這個假設后,就著手實際地(請注意這點)研究材料。他從各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取出一個形態(即商品經濟體系)加以研究,并根據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來研究這些材料)對這個形態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作了極其詳盡的分析。”也就是說,唯物史觀是通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得以實證檢驗的,其檢驗成果就是《資本論》。《資本論》既是馬克思運用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內在規律的結果,同時也是馬克思通過資本主義宏觀樣本數據,對唯物史觀進行實證檢驗的過程。列寧說:“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唯物史觀在剛提出來的時候,“暫時還只是一個假設”。但是在《資本論》問世之后,唯物史觀就是被實證檢驗所證明了的科學理論。由此可見,倘若拋棄了《資本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性又何以可能?倘若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又何以立足?在評論了姚先生的《最新萬字方案》之后,接下來我評論一下公方彬教授有關“誰養活了誰”的困惑。2020年2月24日,《今日頭條》刊登了一篇文章:《公方彬:誰養活了誰?》。由于正忙于學習如何講授網絡課的數字技術,故而對于公方彬關于“誰養活了誰”的看法,我也就一笑了之。后來,有學生提起了這篇文章,并問我:“怎么沒見馬克思主義學者出來質疑和回應公方彬的文章?”于是,我寫下了評論文字,算是對公方彬文章的一個回應。在《誰養活了誰?》中,公教授首先提出了一個困惑:“‘階級仇’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革命階段激發精神力量的來源和邏輯基礎,所謂‘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反抗’,沒有剝削就沒有革命。問題是這個邏輯關系在奪取政權后又發生了哪些變化,是長期延續還是發生轉移?認定處在延續中就等于否定了革命取得徹底成功,認定發生轉移就要回答轉移到了哪里。如此重大而又根本的問題,我們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更未形成嚴密邏輯基礎上的新思想理論體系。”公教授的困惑雖然比較繞,但繞了好幾圈之后的指向,卻非常明確:既然共產黨革命的理由是階級和剝削的存在,那么今天搞改革開放了,階級還存在嗎?剝削還存在嗎?言外之意,改革開放以后,階級和剝削已經不復存在了。對于一個受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育的人來說,階級與剝削在當今是否仍然存在,這難道這不是一個婦孺皆知的常識么?難道這是一個需要“正面回答”的問題么?至于這個常識怎么就成了公方彬教授的困惑,這才是一個“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的、令我感到困惑的問題。對于公教授埋怨的“一直沒有作正面回答”的困惑,公教授自己給出的“正面回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由于經典作家的剩余價值學說深刻闡明了工業革命前期的社會基礎與經濟關系,而引來波瀾壯闊的國際共運。今天來看,這個理論系統解決了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矛盾問題,而沒有解決奪取政權后經濟和社會關系發生變化后的新矛盾新問題(‘馬克思主義沒有窮盡真理,只是開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判斷或基于此)。”這段充滿“馬克思主義語境”的說法比較學術性,所以我有必要簡單解釋一下。在公教授看來,階級和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與人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毫無任何關系;與人們在經濟關系中所處的地位,毫無任何關系。一句話,階級和剝削,與既定社會的經濟結構沒有任何關系。那么,階級和剝削與什么有關系呢?衡量階級和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又是什么呢?對于這個問題,公教授雖然沒有明說,但在他的邏輯中,鑒別階級與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就是看共產黨“需不需要革命”:如果共產黨需要鬧革命,那么階級和剝削就存在著;如果共產黨不需要鬧革命了,那么階級和剝削就自動從地球上立馬消失了。也就是說,鑒別階級與剝削是否存在的標準,完全是“實用主義”的標準:我需要,則用之;我不需要,則棄之。至于這“用之”或“棄之”的東西是否真的存在,那就要看你想要做什么了。公教授的邏輯讓我想起了一個成語故事:掩耳盜鈴。據《呂氏春秋·自知》記載:“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錘毀之,鐘況然有聲。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恕我直言,公教授鑒別階級與剝削存在與否的標準,其實就是“掩耳盜鈴”的標準。在《掩耳盜鈴》里,偷鐘人挪動大鐘的時候,鐘的響聲是客觀存在的,不論偷鐘人是否捂住耳朵,這鐘都是要響滴。同樣道理,在階級社會中,人們總是處于客觀的階級以及階層的層級之中,不論人們是否喜歡,階級以及階級斗爭都不會以某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至于階級之間呈現出什么樣性質的關系(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以及階級斗爭采取什么樣的形式,那是另一回事情。有人把階級斗爭僅僅理解為“打打殺殺”,這是對階級斗爭的曲解。階級斗爭的形式多種多樣,并非只有暴力斗爭。比如,勞資之間的經濟斗爭、文化領域的思想斗爭,以及意識形態的觀念斗爭,都是常見的階級斗爭形式。不知公教授是不是把階級斗爭僅僅理解為“打打殺殺”了?公教授不喜歡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以為只要人們主觀上給予否定,階級與階級斗爭從此就不復存在了。這與那位“掩耳盜鈴”的一樣,都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此,我們必須重溫一下要高度重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級理論。1979年6月,鄧小平在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四川代表團的講話中也指出:“既反對階級斗爭熄滅論,又反對階級斗爭擴大化”。1980年,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有人說,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了,怎么還會有階級斗爭?現在我們看到,這兩方面都是客觀事實。目前我們同各種反革命分子、嚴重破壞分子、嚴重犯罪分子、嚴重犯罪集團的斗爭,雖然不都是階級斗爭,但是包含階級斗爭。”由鄧小平主持制定、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概括:“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夸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此外,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名言中也有“消滅剝削”的重要思想。2014年2月,習近平在《二月講話》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關于階級斗爭問題,《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部分修改)中明確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可見,階級斗爭有可能激化的觀點、階級立場和階級分析的原則,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性和客觀性。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當然沒有窮盡真理,所以需要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在于,用“還需不需要革命”作為判斷階級存在與否的標準,這是不是就發現了真理呢?
比如公教授發現:“‘誰養活誰’的問題將不再是革命階段的工人與資本家、農民與地主,而是納稅人與政府。這看似簡單其實根本,因為關系到思想引導,價值系統建構,及其制度設計與利益分配模式。”這個發現說白了就是:既然今天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了,那么,勞動與資本之間也就不存在“誰養活誰”的問題了;既然當下的勞動者與資本之間“誰養活誰”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那么,階級關系從此也就被納稅人與政府的關系取而代之。如果發現者不是中共黨員,有這樣的發現也不足為怪。如果發現者是“中共黨員”,那么我就沒必要對他重復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了。因為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是每一個中共黨員的起碼要求。如果說發現者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那么他的所謂“發現”就足以證明:要么他不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要么他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二者必居其一。問題是,即便發現者不懂或不信經典馬克思主義基本道理,起碼也應該懂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反復強調“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難道發現者已然忘記了嗎?按照“兩個毫不動搖”的邏輯,我們之所以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并堅持發展公有制絕不動搖,就是因為現在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要不忘初心,要逐步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按照“兩個毫不動搖”的邏輯,我們之所以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就是因為我們必須正確引導、促進符合現階段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系健康發展,而并不是說私人資本從此就不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了,就不追求剩余價值了。總之,有沒有剝削,首先是一個關乎“事實”問題。而怎么評價剝削,則另一個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價值判斷的需要,就不需要實事求是了。這里有必要討論一下公教授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批評。對于貧窮的原因,他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完全解釋經濟領域的復雜現象,有許多方面的問題大值得追問。舊社會窮人很多,赤貧者亦眾,導致的主要原因究竟源自剝削,還是限于資源短缺、生產力低下?比如在農村,有大地主的村莊說貧窮源于剝削,而大面貧困,甚至方圓幾十里也找不出一個富裕戶,這時仍然強調貧窮源于剝削,就缺乏說服力。”公方彬上面的說法,其實是對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的誤讀。所以,我有必要給予澄清:馬克思從來沒有簡單地、片面地、孤立地斷言過:“赤貧多的原因源自剝削”;馬克思主義從來都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從來都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去揭示貧窮的根源;一言以蔽之,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疊加態中,來看待并解決貧窮問題的。對于公方彬所謂“貧窮的原因”,有學者告訴我:“貧窮與剝削并存是歷史事實。難道生產力低下就不會有剝削了嗎?奴隸社會的生產力很低下,奴隸主對奴隸的剝削卻相當殘酷。不能用生產力不發達來否認剝削的存在。”姚洋先生把他期待的“一個統一的政治和哲學理論”,定位在“實用主義”加“儒家思想”。這樣的“哲學理論”到底是什么理論,我琢磨了半天,不甚了了。公方彬教授把否認階級關系的現實存在,作為其“新思想理論體系”組成部分。這樣的“新思想理論體系”究竟與馬克思主義有何關系,我也不甚了了。但有一點我是清楚的:馬克思主義不僅過去沒有認可,現在和將來也不會認可把這樣“一個統一的政治和哲學理論”和這樣的“新思想理論體系”,作為自己“中國化”的理論成果。至于姚先生把“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定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樣的定位僅從馬克思主義常識來看,也是值得商榷的。限于篇幅,我這里就不討論了。某微信群里有位馬克思主義教授說:“《最新萬字方案》消解了馬克思主義,把實踐標準說成鼠目寸光的實用主義,把共產黨人以人民為中心、遵循歷史規律的政治說成含糊不清的‘賢能政治’,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儒家社會’。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社會主義統統被消解了,只剩下大清王朝。”這位馬克思主義教授的話雖然比較尖銳,但是“一針見血”。(作者系《財經科學》常務副主編,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政治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4期)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m.jqdstudio.net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