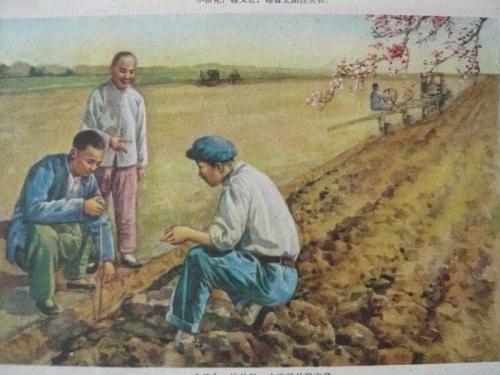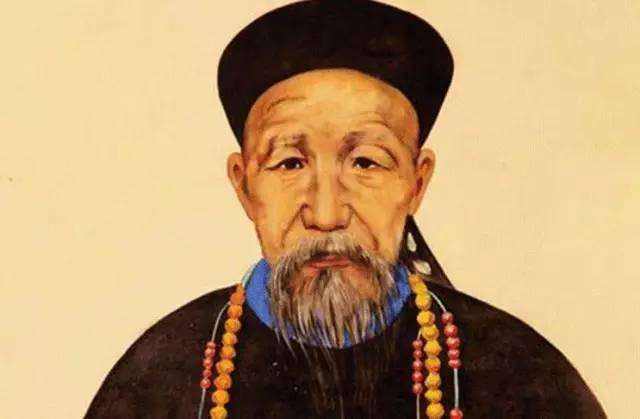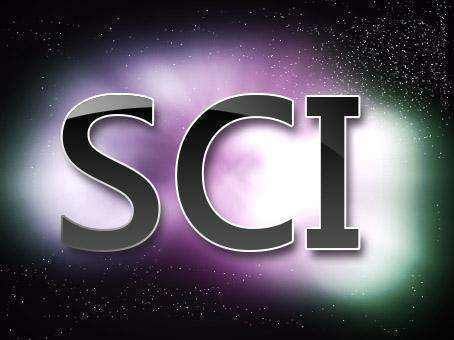在佛羅里達大學癌癥研究大樓四樓,曾經由譚蔚泓教授領導的實驗室一片混亂。白色的實驗服堆在工作臺上,標有生物危害警告的儲物箱零零散散地放在地上。
旁邊的架子上,擺放著幾本指導手冊和實驗記錄,緊挨著的,是譚教授和二十多名學生和員工的合影。照片上,他們面帶微笑。
這是一個二月份工作日的下午,但沒有人在里面工作。與此同時,地球的另一端,一個由 300 名中國科學家組成的科研團隊正在連夜工作,爭分奪秒開發出了新型冠狀病毒快速檢測試劑盒,以便加速臨床檢測效率。目前已經在進行臨床試驗,未來有望實現在非醫療環境下篩查疑似病例。
該項目的領頭人之一,正是譚蔚泓,前佛羅里達大學化學系杰出教授,現任湖南大學副校長、教授。
出現這樣的情況,都是拜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掀起的針對外國資助科研人員的調查所賜。調查主要關注美國科研人員是否涉嫌隱瞞在中國高校、科研機構的職務和薪酬,以及與“千人計劃”的聯系。
據美國非營利新聞調查機構 ProPublica 統計,算上此前從未被媒體披露過的,目前已有佛羅里達大學、MD 安德森癌癥中心、威斯康星大學、埃默里大學和路易斯維爾大學的近三十名科研人員離美返中,其中有的是被開除或實驗室被關閉,有的則是在調查期間主動離職或離境。
譚蔚泓屬于后者。他所在的佛羅里達大學 2019 年 1 月收到了 NIH 的調查函,隨即對他在中國的工作情況展開了調查,包括他在湖南大學的職務、薪酬、科研資助和“千人計劃”項目等等。在被調查期間,他選擇辭職并返回中國,在湖南大學繼續他的科研生涯,同時任副校長,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根據湖南大學官網介紹,他在國內的教職早在 2000 年就已經開始,曾兼任過湖南大學化學化工學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生物醫學工程中心兼職常務副主任、生物學院院長等職務。最近一次變動是 2017 年 8 月,擔任副校長一職。
未披露的中國教職
譚蔚泓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生物分析化學、化學生物學和生物醫學工程,曾是 NIH 資助的明星研究員和項目領頭人,在佛羅里達大學工作超過 25 年,獲得過許多國家和國際級化學獎項。
目前在佛羅里達大學官網上,譚蔚泓的名字仍出現在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s)列表中,還可以搜到他實驗室的相關信息,頁面顯示最近一次更新停留在 2019 年 3 月。其研究團隊主要關注癌癥以及學習和記憶問題,涉及三個研究領域:生物納米技術、分子工程和化學生物學。
據佛羅里達大學化學系的匿名員工透露,每年系里都會根據研究成果和科研經費等指標評估教職員工,自 1996 年加入化學系以來,譚蔚泓通常都是排名前三的教授。他與學校的系主任和高級科研人員關系密切,而且還深受學生喜歡,經常能看很多學生在他辦公室門口等著見他。
圖 | 譚蔚泓實驗室主頁,還能在大學官網上找到(來源:佛羅里達大學)
譚蔚泓的英文履歷顯示,他自 1993 年以來就和湖南大學建立了聯系,一直是兼職教授身份(Adjunct Professor)。這是履歷中唯一與湖南大學有關的職務。
從獎項和科研成果發表時間來看,履歷的更新時間可能是 2012 年左右。結合湖南大學網站上的職務歷史,他當時應該兼任了生物學院院長和化學生物傳感與計量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但英文履歷上均沒有提及。
2019 年 1 月,NIH 通知佛羅里達大學,譚蔚泓可能與外國機構和研究資金存在未披露的關系,要求大學相關部門發起調查。
調查人員開始審查譚蔚泓的郵箱記錄和其他信息。他們發現,譚蔚泓偶爾會使用佛羅里達大學的郵箱進行與湖南大學相關的工作,還有郵件證據顯示,他至少收到了四筆中國科研資金而未披露給 NIH,還協助招募其他美國研究人員加入中國的人才計劃。此外,譚蔚泓也向調查人員解釋了自己在湖南大學的工作情況。
不過,在向大學提交的年度披露報告中,譚蔚泓確實報告了在中國的職務和收入。2017 年,他披露自己每周在湖南大學工作 10 小時,薪水為 3 萬美元。2018 年,工作時長增加了一倍,薪水為 5 萬美元。而在 2019 年,他報告自己每周在湖南大學和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分子醫學中心工作 20 小時。這些職務的總薪酬約為 12 萬美元。
圖 | 譚蔚泓的英文履歷,只有一項兼職教授與湖南大學有關(來源:佛羅里達大學)
隨后,調查人員將有關他和其他兩名學者的信息提交給了一個負責審核公共資金資助項目受外國影響的特別州立法委員會。報告中沒有直接提及他們的名字,而是用“教職員工 1,2,3”這樣的代號指代。這份報告目前已經納入到美國聯邦發起的更廣泛調查活動之中。
據 ProPublica 披露,報告中代號為“教職員工 1 號”的背景資料(包括聘用日期、研究領域、科系和中國機構)都與譚蔚泓的背景一致。
在回應 ProPublica 時,譚蔚泓拒絕回答有關他離開佛羅里達的問題,但提供了文件證明大學系主任曾在 2015 年支持他在中國的研究工作。
這是一封佛羅里達大學前化學系主任 William Dolbier 撰寫的推薦信,為了幫助譚蔚泓申請中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信中寫道,“我們很高興看到他在湖南大學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功,我們非常支持他在那的研究和教育工作。”最終他成功當選院士。
ProPublica 還采訪了譚蔚泓的美國同事。一些人表示,最近幾年他在中國的工作明顯增加,經常到中國出差,有時每個月會回去兩次。他的解釋是中國的工作和佛羅里達的研究形成了很好的互補,因為在中國對人體測試更加容易,他在美國的研究更多地專注于不涉及患者的基礎科學測試。
另一名同事還表示,譚蔚泓曾向他表達過中國工作量的增加讓他感到了壓力,一度考慮無薪請假一段時間。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向大學提出過申請,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去年的辭職決定是非常突然的,也沒有向同事透露具體原因。
如今回到中國的譚蔚泓教授和另外兩支研究團隊迅速行動,合作開發了一種可以在 40 分鐘內給出測試結果的試劑盒,適合用于非醫療環境下的快速核酸檢測,幫助非醫療專業人士快速篩查潛在患者。
公開資料顯示,該項目已被推薦納入中國藥監局應急審批通道,截至 2 月中旬完成了 100 多例臨床測試,陽性樣本的檢出率約為 90%。一個月前,科研團隊正在進行產品的優化和定型,希望實現普通民眾的家庭自檢,避免醫療資源擠兌和交叉感染。未來還有望推廣成其他突發急性傳染病的防控手段。
譚教授的佛羅里達大學前同事也知曉這項成果,有人表示自己看到過他分享的 13 頁診療手冊,里面介紹了試劑盒的技術原理和優勢。
之前為譚蔚泓撰寫過推薦信的前化學系主任 William Dolbier 認為,如果他能坦白自己在中國的所有工作,或許可以避免離開。“他沒有試圖從美國竊取什么,研發這類藥物才是他的主要重點和目標。他跟我說過,愿意讓新的 COVID-19 試劑盒也可以在美國使用。”
ProPublica 在報道中稱,“病毒檢測是減緩疫情蔓延的關鍵,但美國遠遠落后于中國”。
人才流失和個人取舍
根據 ProPublica 的調查,除了比較有名氣的納米學泰斗 Charles Lieber 和知名生物學家李曉江、李世華等人,還有 20 多名教授因未向 NIH 披露與“千人計劃”的聯系而遭到調查,而媒體從未報道過他們。
在 2018 年之前,NIH 更愿意將中國視為生物醫學研究的合作伙伴,甚至在 2010 年還與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建立了正式合作伙伴關系,鼓勵兩國高校合作。雙方共同資助合作項目,支持中美兩國科學家在腫瘤、過敏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包括 HIV/艾滋病及其并發癥)、醫學免疫等研究領域開展合作。
即使到 2019 年,NSFC 與 NIH 的合作也在正常開展,只不過獲批資助的項目數僅有 13 個,降至一個歷史低點。
根據 NSFC 網站信息:NSFC 與 NIH 分別負責資助本國科學家的研究經費及開展雙邊交流所需的出訪國際旅費和國外生活費。NSFC 的資助強度為直接費用每項不超過 300 萬元,NIH 對每個項目資助強度為直接費用不超過 75 萬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雙方的合作產出了很多人類疾病領域的重要研究和領軍人物。DeepTech 查詢顯示,僅以此次參與抗擊新冠肺炎的知名專家為例,被譽為“硬核”醫生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復旦大學教授盧洪洲都是 2011 年合作項目入選者;而廣州醫科大學鐘南山則入選了 2016 年的合作項目。
圖|“硬核”醫生張文宏入選 NSFC 與 NIH 在 2011 年批準的合作項目。(來源:NSFC 網站)
圖|廣州醫科大學鐘南山則入選了 2016 年的合作項目(來源:NSFC 網站)
然而近年來,通過審查獲得聯邦資助的研究人員的背景,NIH 發現了許多未公開的外國聯系,尤其是與中國研究機構的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未被披露的學者雖然被 NIH 調查,但都是針對未公開的科研資助或職務,他們均未受到竊取研究成果或非法知識產權轉讓的指控。
事實上,這兩者的聯系可能很微弱。
通常來講,面對 NIH 對非公開披露資料的質疑,大學應當承擔部分責任,因為教職員工會定期向大學披露利益關系,而大學在提交給 NIH 之前,需要負責驗證信息的準確性。
“在大學,這些信息驗證程序和利益關系的披露規定,長久以來都沒有嚴格執行,”NIH 院外研究副主任 Michael Lauer 表示。
顯然,NIH 很清楚這一點,但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授意下,有意將其上升到新的高度,嘗試將隱瞞科研資助和竊取科研成果聯系在一起,敦促科研機構加大審查力度。
佛羅里達大學向州和聯邦調查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還包括了另外兩名員工:生物醫學工程教授 Lin Yang 和兒童癌癥研究助理教授 Chen Ling,代號分別是“教職員工 2 號”和“3 號”,排在“教職員工 1 號”譚蔚泓之后。
圖 | 2014 年,Lin Yang 教授受邀加入佛羅里達大學工作
兩人均在去年調查開始后離職。其中 Lin Yang 教授回復了 ProPublica,稱自己不認可大學的調查結果,因為自己雖然申請了中國的人才計劃,但并未入選。而且在佛羅里達工作期間,從未在中國獲得任何資助和教職任命。
Yang 教授的律師對此評論稱,“佛羅里達大學自 2010 年開始大力鼓勵海外合作,(當事人)因大學要求的事情而蒙受懲罰是說不過去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優秀人才流失。”
如果說因為隱瞞科研資助才會被 NIH 盯上,那么路易斯維爾大學的神經生物學邱猛生(Mengsheng Qiu)教授似乎不應該成為目標,至少在他的同事和妻子眼中如此。
根據 ProPublica 的調查,邱猛生是路易斯維爾大學的終身教授,自 2009 年加入“千人計劃”,開始在杭州師范大學兼職。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他獲得了 NIH 和 NSF 的多項資助,累計科研經費超過千萬美元,還是多個學術期刊的審稿人。他的前系主任 Fred Roisen 給予了他高度評價,稱其是出色而敬業的學者。
圖 | 杭州師范大學網站上的邱猛生教授簡介
據 Roisen 透露,邱猛生不僅向大學披露了兼職工作和薪酬,甚至還通過主動減薪的方式來抵消自己在中國的收入——他在中國工作時,路易斯維爾大學不會付他薪水。
這一點得到了邱教授妻子 Ling Qiu 的側面印證,“他每次去中國訪問都得到了大學的批準,資金由中國提供。美國這邊希望他上報一切信息,他說他做到了,沒有做錯任何事,對調查感到十分沮喪。”
熟悉他的同事表示,自 2019 年夏天以來,NIH 和大學一直在對他進行調查。路易斯維爾大學發言人 John Karman III 拒絕置評,稱“不會評價正在進行的調查”。
去年 12 月,邱教授選擇從路易斯維爾大學退休,回到杭州師范大學擔任全職教授和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
“在 2019 年與杭州師范大學續簽合同時,大學要求他考慮成為全職教授的可能性。再結合 NIH 的調查,迫使他不得不在中美之間做選擇,”邱教授的朋友表示。“一番取舍,他才最終下定決心。他更喜歡在中國工作,那里的實驗室條件和學生都比路易斯維爾更好。”
-End-
參考:
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the-trump-administration-drove-him-back-to-china-where-he-invented-a-fast-coronavirus-tes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美國有錢有勢的人能優先檢測新冠肺炎 特朗普默許不公存在:也許這就是人生
2020-03-23徐倞:在美抗疫日記:群體感染而不是群體免疫在美國可能成為現實
2020-03-22? 昆侖專題 ?
? 十九大報告深度談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