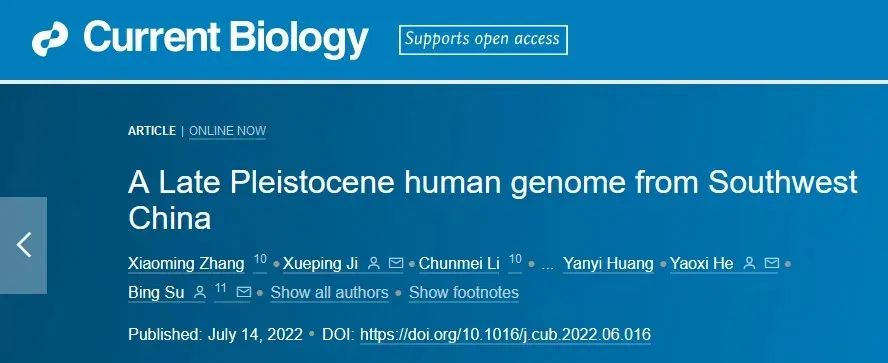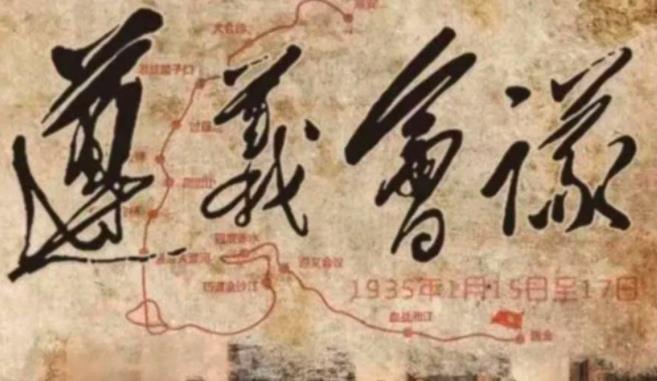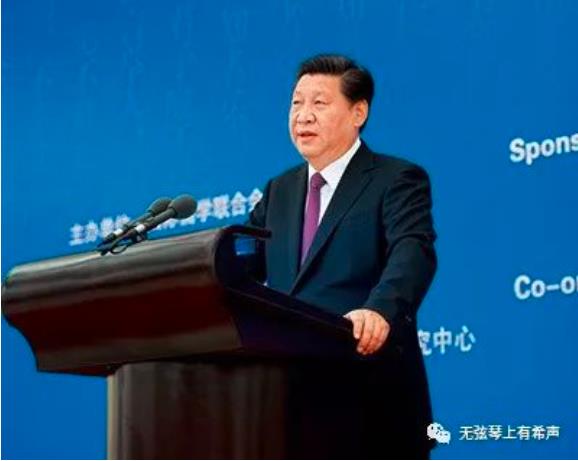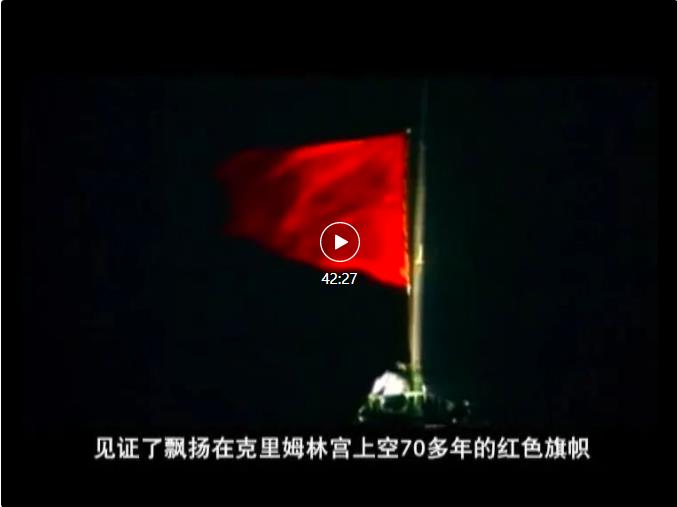說到頭一個晚上我在武大做的線上講座《馬克思反對“從實際出發”嗎?》,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現在都馬斯克了,你還講什么馬克思?”朋友說:“你的馬克思是搞純理論的,人家馬斯克是搞高科技的。”我很納悶,難道有了會編程序的碼農,從此就不能講愛因斯坦了么?我說:“搞純理論的馬克思同志,比你那個搞高科技的馬斯克先生,要牛得多。”我說:“因為馬斯克不知道,而馬克思卻知道: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乃是鐵的必然性”。昏暗的天地之間,大型的露天看臺上,坐滿了觀看表演的男女觀眾,觀眾的眼里全是貪婪的欲望。在看臺的正中,坐著一些沒有頭顱的身軀,衣服領子空空如也,正等著PS頭顱。一個聯想浮上我的心頭:這些怪異而恐怖的身軀,不就是資本主義世界中輪流執政的政要嘛!我好奇地看著人頭攢動的看臺:這PS的頭顱將從哪里來呢?不知道什么時候,一些頭顱仿佛從十維空間中冒出來,挨個兒插在那些衣領空空如也的身軀上。于是乎,頭顱的臉上立馬露出了陰森森的活氣。哦,原來是美式和港式電影里面,嘴上叼著大號雪茄的成功人士,脖子上掛著黃金項鏈的金融大亨,手指頭帶著鉆戒的黑白老大。這個時候,天空中零零星星地飄灑著什么東西,不是雨,是美鈔。坐在看臺上的千萬男女,潮水般地突然歡呼起來。跟隨著騷動人群的灼灼目光和瘋狂的手勢,我看見化身為總統的金主站起身來,洋洋得意地向觀眾揮手致意。記得在觀眾的歡呼聲中,我痛苦地閉上眼睛:“難道,以金錢作為唯一衡量標準的資本主義,是人們心甘情愿的選擇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在做這個夢的白天,我恰好給博士生上了《高級資本論》課程。
——“趙老師,我有一個疑惑。馬克思說,‘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問題是,雇傭工人如果有出息的話,也可以成為資本家嘛,也可以去占有別人的剩余價值嘛!”
這位90后的意思是說: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天經地義。在西方經濟學的強力灌輸下,不少人早已習慣用這樣的邏輯來思考問題:你有本事,你就勝出成為資本家;你沒本事,你就失敗淪為打工仔。所謂“剝削”,實乃游戲規則的必然結果。世界就是這么現實,失敗者沒必要嘰嘰歪歪。主流經濟學有一個信條:資本主義金錢社會是大多數人喜歡的社會。資本主義肯定是某些人喜歡的社會——比如,那些自以為能成為“人上人”的人精,但它并不是人們自愿選擇的社會。資本主義當然比封建社會具有進步性和正義性,但與其說資本主義是人們的自愿選擇,不如說它是歷史必然性強加給人類的社會。韋伯從倫理精神來溯源資本主義,他把資本主義歸結為新教的產物。與韋伯膚淺的溯源相比,馬克思則從生產方式來解剖資本主義,他把資本主義歸結為歷史必然性的產物。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有過如下廣為人知的論述:
——“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
馬克思說“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并不意味著馬克思認同這些關系下的惡俗“三觀”,更不意味著“拜金主義”的衡量標準就值得嘚瑟。因為,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目的改變不了歷史規律的作用方向:
——“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
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鐵的必然性”,就是歷史決定論,也就是馬克思所說:
——“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
所謂“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人類社會的這個演化邏輯,不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決定論嗎?既然歷史“有規律”,那么歷史就必然是被規律所“決定”的;既然客觀規律是事物內在的必然因果聯系,那么承認歷史是受到規律制約的“自然過程”,就必須承認歷史決定論的強制作用【1】。奇怪的是,很多人承認資本主義的興起具有“鐵的必然性”,卻拒不承認資本主義的消亡也具有“鐵的必然性”。
——“美國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支持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很多年輕人卻寧愿擁抱資本主義。”
他從手機里翻出了一張照片:信奉社會主義的美國參議員桑德斯,年輕時因上街示威游行,被兩個美國警察扭住胳膊。照片中留著長發、穿著喇叭褲的青年桑德斯十分瘦小,在兩個穿著制服的彪形大漢的左右挾持下,顯得有些滑稽。然而,給我看照片的年輕人卻無比驕傲地贊嘆:“真酷!”我問:“既然美國青年大都支持桑德斯,他為啥競選失敗了?”他有些遺憾地說:“美國50、60年代出生的人屬于保守的右翼,如果不是他們把選票投給瘋子特朗普,桑德斯這個社會主義者已經勝出了。”他非常堅定地告訴我:“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越來越傾向社會主義。未來是年輕人的世界,所以未來是社會主義的世界。”我也不知道,這位中國青年以及美國青年所向往的社會主義,到底是民主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社會主義?至于選票能不能迎來社會主義的未來,這個另說。但是對于社會主義前景的“鐵的必然性”,我和他是有共鳴的。給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旦說到“很多中國年輕人寧愿擁抱資本主義”,這位從美國回來的留學生就很不以為然,且充滿了憂慮。當我們驅車經過成都最有現代氣息的天府新區時,他指著密集的高樓和人來人往的打工仔說:
——“現在的年輕人早九晚五打拼,幾個人合租幾十平的鴿子間,多數只能糊口而已,談何發展?青春就在996中消耗掉,一直到老,希望何在?”
現在大家都在談“共同富裕”,這的確是中特社會主義應當關注的重大問題。然而,如果就業問題得不到解決,談何“共同富裕”?所以,去年我在一篇論文中提出預警: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雇傭勞動制度越來越難以解決勞動者的就業問題,這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內生矛盾的必然結果,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外在表現。換言之,在雇傭勞動制度的條件下,越來越嚴峻的就業形勢基本上就是一個無解的難題。”【2】
不幸的是,我的預警正在被現實所證實。據報道,2022年4月13日,北京市朝陽區公布了公務員擬錄用人員名單,其中:
——酒仙橋街道的城市管理執法崗,由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女博士王夢珍競聘成功。
——崔各莊街道城管監察崗,由一名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碩士畢業的海歸競聘成功。
——“現在清華北大的碩士、博士,都來卷成都的中小學教師崗位了。”
——“雙流一所很普通的中學老師說,他們學校小學部招聘編外教師,2000多人投簡歷,本碩985+211的就有五六百人,第一輪簡歷就刷掉一千多人……”
宏觀數據也從總體上說明了年輕人的就業形勢很嚴峻。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凌暉說:“今年6月份,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9.3%”【3】。“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不是說好的56789么?不是說好的“私企是解決就業的最優路徑”么?持續的疫情固然是就業形勢惡化的因素之一,但雇傭關系就業模式內在矛盾的發展,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從來也不擔心失業的體制內的飽學之士,在微信群里為雇傭關系的就業模式辯護:“內卷就是競爭,沒有內卷哪有競爭,哪來的發展動力?”呵呵,這個“發展動力”是如此強大,以至于年輕人打破腦袋也要爭搶“鐵飯碗”。難道內卷的偉大成效,就是要把年輕人都逼進“體制內”,去端“鐵飯碗”不成?為內卷辯護的飽學之士是否看到,正是你們所崇尚的“發展動力”,造成了幾近無解的矛盾局面:
一方面,90后的碩士博士們堅信:“生存競爭,優勝劣汰,天經地義”,發誓要“生命不息,內卷不止”;
另一方面,畢業后的年輕人無不爭先恐后地擠進“鐵飯碗”單位,沒有一個愿意被“天經地義”的動力卷成肉醬。
什么是“鐵飯碗”?在改革開放的語境中,“鐵飯碗”就是傳統社會主義“大鍋飯”的代名詞。這里插一句。我指導的一個碩士畢業生,在經歷了慘烈的內卷之后,終于把自己卷進了國家開發銀行。接到錄用通知,她哭了。為什么哭?因為國開行是“鐵飯碗”!都“優勝劣汰”成這個樣子了,就業前景堪憂的年輕人還會“寧愿擁抱資本主義”嗎?當內卷的動力已經不能制造飯碗,而只能制造兩級分化的時候,現行的游戲規則還能持續下去嗎?
【1】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可參:趙磊 等《唯物史觀:歷史目的論抑或歷史決定論》,載《社會科學研究》2021年第5期。【2】趙磊《論共同富裕的三個基本問題》,載《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21年第11期。【3】《16-24歲青年人失業率創新高,統計局回應》,《鳳凰新聞》(財經頻道)2022年7月15日。(作者單位:西南財經大學;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