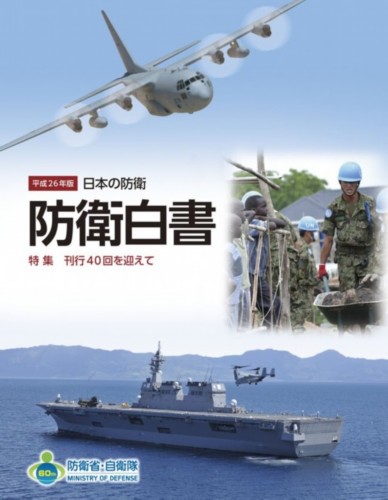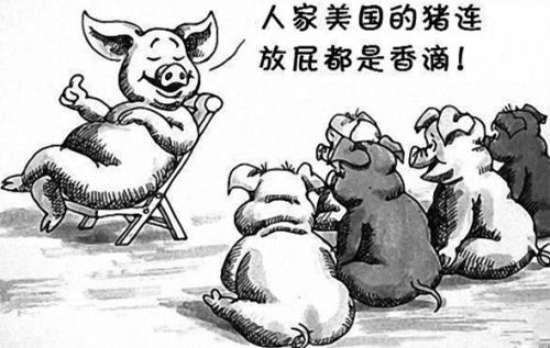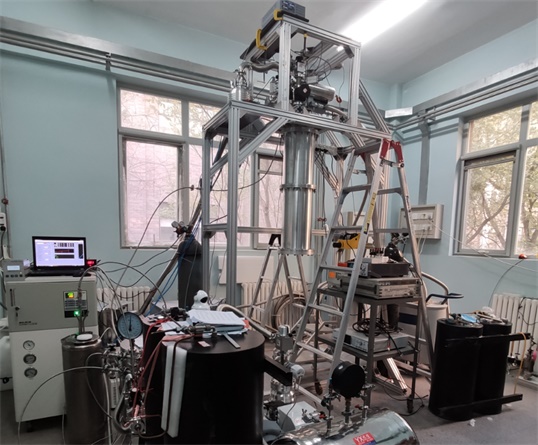從海地總統被暗殺到古巴爆發示威游行,都是美國在背后組織、策劃,干這種事對美國來說是駕輕就熟,特別是在整個美洲,美國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美國一直將整個拉丁美洲視為美國的后院,視為美國人的美洲。

所謂國際分工就是指一些國家專門贏利,而另外一些國家專門遭受損失。地球上我們所居住的這一地區一一今日我們稱之為拉丁美洲,過早地成熟了,自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越洋過海吞噬這一地區的遙遠時代起,拉丁美洲就淪為專門遭受損失的地區。幾個世紀過去了,拉丁美洲完善了它的作用。它不再是奇妙的王國,在這里,現實曾經打破神話,戰利品、金礦和銀山曾超出人們的想象。但拉丁美洲仍起著附庸的作用,繼續為他人之需要而存在,成為富國的石油、鐵礦、銅礦、肉類、水果、咖啡、原料、糧食的產地和倉庫。富國從消費這些原料中所得到的利潤遠遠超過拉丁美洲在生產這些原料的過程中所獲得的利潤。原料購買者征收的稅款大大高于原料銷售者的收入。貿易越是具有更多的自由,就越是需要為蒙受貿易損失的人修筑更多的牢籠。我們的審訊和執法制度不僅為處于統治地位的國外市場而運轉,還從被人主宰的國內市場所得的外國貸款和投資中提供源源不斷的大量利潤。1913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告誡道:“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他深信:“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
在此過程中,我們甚至失去了被稱作美洲人的權利,盡管在“五月花”號的移民定居普利茅斯沿海地區的一個世紀之前,海地人和古巴人業已作為新的種族而被載入歷史。今天對世界來說,美洲就是美國,我們充其量只是居住在一個身份模糊的美洲次大陸,一個二等美洲的居民。
拉丁美洲是一個血管被切開的地區。自從發現美洲大陸至今,這個地區的一切先是被轉化為歐洲資本,而后又轉化為美國資本,并在遙遠的權力中心積累。對那些將歷史看作一部競爭史的人來講,拉丁美洲的貧窮和落后就是在競爭中失敗的結果。我們失敗了,別人勝利了。但實際上,只是因為我們失敗了,他們才獲勝。正如人們所說,拉丁美洲不發達的歷史構成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我們的失敗總是意味著他人的勝利;我們的財富哺育著帝國和當地首領的繁榮,卻總是給我們帶來貧困。殖民地和新殖民時期的煉金術使黃金變成廢銅爛鐵,糧食變成毒藥。波托西、薩卡特卡斯和黑金城從生產貴金屬的光輝頂峰跌入被掏空了的礦井深淵。毀滅是智利硝石礦和亞馬孫橡膠林的命運,巴西東北部的甘蔗園、阿根廷的栲樹森林和馬拉開波湖一些石油村落的命運,都以令人心酸的理由使人相信,自然界賦予的、被帝國主義掠奪走的財富不是終古存在的。滋潤著帝國主義權力中心的雨水淹沒了該體系廣闊的外圍,與此同時,我們的統治階級(受外部統治的國內統治階級)的舒適安逸就等于詛咒我們廣大民眾永遠要過著牲口般的生活。
到20世紀末,美國的人均收入將是拉丁美洲的十六倍。整個帝國主義體系的力量是以局部必須不平等為基礎,這種不平等達到越來越驚人的程度。在日益擴大的差異的推動下,按絕對水平計算,壓迫別國的國家變得越來越富有,如按相對水平計算,它們則變得更加富有。中心資本主義可以制造并使人相信有關它富裕的神話,但是神話不能當飯充饑。構成資本主義廣大外圍的窮國對此是十分清楚的。一個美國公民的平均收入是一個拉美人的八倍,并以十倍于拉美人的速度增長。而且,由于布拉沃河以南拉美地區的廣大窮人和少數富者之間存在著無底深淵,各種平均數使人迷惑。我們的統治階級始終被引入帝國主義權力的星座之中,他們毫無興趣來調查一下愛國主義是否比賣國主義更有利可圖,或者研究一下國際政策的唯一做法是否就是乞求他人。因為“別無他法”,國家主權被抵押出去了。寡頭集團的種種借口是為了別有用心地將一個階級的軟弱性同每一國家所謂的缺乏使命混淆起來。
一個多世紀之前,一位危地馬拉外交部部長曾預言:“從給我們造成不幸的美國產生擺脫不幸的出路,這是令人奇怪的。”
在拉美漫長、痛苦的歷史中,所有遭扼殺或被出賣的革命幽靈重新出現在新的革命歷程中,過去的矛盾揭示并孕育了今天的時代。歷史是回首往事的先知。它根據贊成和反對的往事預告未來。所以,本書想提供一部掠奪的歷史,同時還要述說目前的掠奪機制如何運轉,征服者如何乘著三桅帆船來到,以及不久前技術官僚們如何乘著噴氣式飛機來到;還要講講埃爾南·科爾特和海軍陸戰隊,西班牙總督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使團,奴隸販子的贏利和通用汽車公司的利潤。同樣,本書也將向人們展示失敗了的英雄和我們時代的革命,揭露丑聞,再現死而復燃的希望:前仆后繼的獻身精神。亞歷山大·馮·洪堡考察波哥大(Bogota)高原古老的印第安風俗時,得知印第安人將在宗教儀式中祭祀用的人稱作“基皮卡”,意即大門,也就是說,每一個被選中者的死意味著又一個新的為期一百八十五次月圓的開始。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自然條件最優越的大陸之一,也是人民最窮困的大陸之一。貧窮的原因不是由于那里的人懶惰,甚至主要也不是領導層的昏庸無能。制造“原罪”的魁首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祖宗--殖民主義制度。《血管》告訴我們,當年大西洋上開往歐洲大陸的船只裝載的每一種貨物,都為一個后來的拉美國家規定了命運。瘋狂的人力、物力資源的掠奪造成拉美大陸上“哪里越是富得不能再富,哪里就越是窮得不能再窮”的人類文明悖謬。
玻利維亞高原上有一座海拔五千米的山峰,叫波托西,山腳下就是當年震驚歐洲的同名銀城,其名聲之大,成就了一句古老的諺語,并見于著名的小說《堂·吉訶德》:“其價值等于一個波托西。”由于發現銀礦,至1650年波托西已擁有十六萬居民,是當時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城市之一。17世紀初,全城已擁有三十六座裝飾豪華的教堂、眾多的賭場和十四所舞蹈學校。1608年,波托西為慶祝宗教節日上演了六天喜劇,舉行了六場化裝舞會,進行了八天斗牛。但是,波托西現在的人口是四個世紀以前的三分之一,是這個世界上著名窮國最貧窮的城市之一。人們與衰亡的礦山共命運,在廢石堆和舊巷道里尋找一點含錫的碎礦。白銀是沒有的,連一點閃亮的東西都沒有,西班牙人撤走的時候用小笤帚把波托西五千個礦井掃得干干凈凈。波托西對面有一座被當地人稱作“瓦卡奇”的山,即“哭泣過的山”,從山上的泉眼里流出的清泉曾供礦工飲用。“瓦卡奇”是波托西被毀的沉默的證人,是它眼看著波托西怎樣一天天地萎縮,改變顏色。
然而當年是美洲的白銀養活了整個歐洲。波托西“至今是美洲殖民制度留下的一道流血的傷口,一份控告書。世界必須以請求它的原諒重新開始”。
還有“白色金子”的悲慘故事。自從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把甘蔗根從西班牙帶到美洲大陸,三個世紀內,這片大陸就成了為歐洲市場提供蔗糖的種植園。巴西東北部含有豐富礦鹽和腐殖層的沿海熱帶林區首先被看中,至17世紀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蔗生產國,與此同時,森林、植被和動物都在單一作物的祭壇上成為甘蔗的犧牲品。當此地的地力耗盡之后,荷蘭人把從巴西學來的技術用于巴巴多斯更肥沃的土地上,從非洲販進大批更健壯的黑人奴隸,取代了巴西東北部的甘蔗生產。從此以后,這塊昔日的寶地變成了巴西最貧困的地區,孩子們經常吃的是木薯粉和菜豆,由于這類食品缺少礦鹽,孩子們出于本能的需要吃起泥土來,大人們不得不給他們套上牲口用的口套,或是把他們放在柳條筐里吊得高高的。這就是延續了幾個世紀并存在至今的、歐洲人所說的“非洲惡習”之一。
16世紀的殖民主義者把印第安人不堪忍受非人待遇而集體自殺的悲慘狀況說成是“為了娛樂和逃避勞動”,20世紀70年代,歐洲有人繼續把這種污蔑當成學術解釋之一,宣稱今天的古巴人繼承了這一遺傳基因。
在危地馬拉的歷史上,歐洲中間商為了招募大量農業季節工,帶著樂隊和烈酒來到印第安人居住的高山,把他們灌得酩酊大醉后,讓他們在賣身契似的合同上畫押;而今天,被冠以“嗜酒如命”之惡名的只是印第安人。
《血管》就這樣讓我們看見了殖民主義與種族歧視的隱秘親緣。
西班牙人走了,英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歐洲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規模集中國際財富,卻妨礙了被掠奪者跳躍到積累工業資本的階段。當獨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試圖起步時,英國人又向他們舉起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的雙面魔鏡,就像后來的美國人揮動的民主自由變色旗—有利的一面總是朝著自己。英國在自己的紡織工業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羊毛的本國公民判以斷其右手,再犯者處以絞刑的酷刑。在教區牧師證明裹尸布系國貨之前,禁止將死人下葬。但是當拉丁美洲的門戶在19世紀初剛一打開,英國人就迫不及待地向具有悠久游牧傳統的阿根廷大草原出口所有馬具,包括英國制造的阿根廷民族服裝“彭喬”(一種騎馬時穿的斗篷),向木材豐富的巴西出口即可入殮的棺材,向他們的熱帶沿海地區出口毫無用處的冰鞋,向仍無紙幣的國家出口高級錢夾。被收買的獨裁政府“像拉皮條介紹淫婦那樣將整個國家拱手讓出”,關貿協定上“ 政治”被草率地譯成“警察”。在西方國家的“援建”下,拉美許多國家的鐵路網呈扇面通往面向歐洲的港口,港口的背后卻是一片毫無內部聯系的沙漠。
英國人走了,美國人來了,拉丁美洲的命運依然如故。
19世紀初,拉丁美洲“獨立之父”玻利瓦爾不無道理地把美國人稱作“美洲的英國人”:20世紀初,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斯也曾做出過鮮為人知的斷言:“美國已經把《獨立宣言》徹底吐了出來。”五百年的歷史給藕斷絲連的西方文明打了一個大問號,如果作為資本主義本質的利己哲學沒有發生變化,那么所謂“進步”和“現代化”不過是思維方法和手段的進步與現代化。《血管》雖然初版于20世紀70年代,但是沒有任何理由使我們相信世界發生了根本變化,《血管》的經典意義正存在于此。
在《血管》里,美國掠奪拉丁美洲的例子不勝枚舉,殘酷手段令人發指。有一段文字使我過目不忘。20世紀60年代軟弱的巴西政府以缺乏資金為名,準許美國空軍在蘊藏著豐富戰略性礦產的亞馬孫平原上空拍照。美國空軍使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獲取了所有重要情報。此后不久巴西兩千萬公頃的土地被出售或強占。這片土地的分布很奇特,它“呈條帶狀,把亞馬孫地區同巴西其他地區隔離開來”根據巴西國會的調查和陸軍部的證詞,美國政府鼓勵這種做法的企圖是在巴西境內開辟一條新邊境,向這一地區定向殖民,秘密開發釷、鈾、黃金、金剛石等重要礦產。二+多個美國新教傳教團在稀有礦產蘊藏豐富的地帶定點傳教,教授英語,并在這片地球上最大的可居住而荒無人煙的地區大量發放避孕藥品。
在中國經濟改型之際,當一些人急于與世界文明接軌”時,讀一讀《血管》中“掠奪的現代結構”一節不無裨益,那里有他人的歷史教訓。我們可以讀到,在誕生于美國、總部設在美國并為美國服務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里,拉美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票數不及美國所掌握票數的一半,因此不得不接受該組織即美國的“指導”,陷入不斷接受貸款、外債高筑的惡性循環。在由拉美國家提供大部分普通資金的泛美開發銀行里,他們的總票數不足通過重要決議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數,而美國獨家擁有否決權,美國政府的內部報告承認,這一否決權使他們得以向包括大學改革在內的拉美事務施加壓力。我們還可以讀到,從1964年起,每一任世界銀行行長都是美國著名商人;以此類推,還有國際開發署等,無一例外。《血管》還以大量事實和細致的分析揭示,所謂的“合資企業”如何控制拉美國家的經濟和技術命脈,像19世紀的鐵路一樣有毒的現代科技如何不科學地在拉美國家制造失業大軍,擴大技術差距。汽車工業戰、速溶咖啡戰,一個個驚險小說般的例證解構了精密的現代掠奪方式。
現在,美國又開始在海地和古巴搞暗殺和顏色革命,我們只能為拉丁美洲人民感到悲哀,同時我們也會為古巴人數十年來在與美帝國主義斗爭中表現出來的抗爭精神表示欽佩。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李光滿冰點時評”;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m.jqdstudio.net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作者 相關信息
內容 相關信息
李光滿 | 從海地到古巴,從暗殺總統到顏色革命:殖民者是如何切開拉丁美洲血管的?
2021-07-14?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