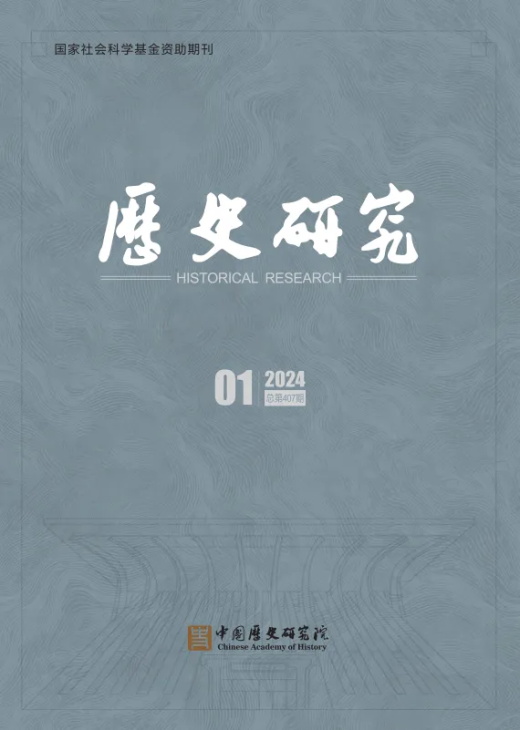摘要:縣制起源是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研究的核心問題。西周王畿“千里”,始封諸侯“方百里”,形成周室對諸侯的優(yōu)勢力量對比。周雖普行分封,但不排斥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實(shí)際呈現(xiàn)為王權(quán)主導(dǎo)下“公邑—私邑”復(fù)合制。東周以降,諸侯縣制形成不同系統(tǒng)。楚縣多屬滅國的直接轉(zhuǎn)化,內(nèi)部變動(dòng)較小,可稱“國”、“都”。晉縣不是卿大夫采邑,也不兼具公邑、封邑二重性質(zhì),實(shí)際是君主直轄公邑,晚期任官、司法與秦漢接近。秦商鞅變法全面推行縣制,徹底實(shí)行公邑化,統(tǒng)一置令、丞、有秩吏,縣制最終確立。中國古代分封制、郡縣制不宜截然兩分。縣制形成與社會(huì)組織、經(jīng)濟(jì)制度變動(dòng)有關(guān),核心是官僚組織的建立及運(yùn)行。
一、問題提出及概念引入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縣制起源是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對于思考郡縣制形成發(fā)展、國家地方治理早期變遷頗具意義。關(guān)于縣制起源,古人已有歸納辨析。今人以顧頡剛、增淵龍夫探討較早,對中日學(xué)界影響甚巨。顧氏將縣制分作兩種類型:秦、楚縣制相近,滅國而立,由君主直轄;晉、齊、吳縣多是卿大夫封邑。增淵龍夫認(rèn)為春秋晉縣兼具封邑和公邑兩種性質(zhì),“以之為縣”的途徑是破壞邑內(nèi)原有氏族秩序,甚至遷出原住民。后續(xù)研究注重三個(gè)方面:一是概念歸納及階段劃分,如分作縣鄙之縣、縣邑之縣、郡縣之縣;二是類型區(qū)分與生成方式,如分為王畿與諸侯不同區(qū)域,又如分為楚縣、晉縣、秦縣等不同系統(tǒng);三是實(shí)現(xiàn)途徑及結(jié)構(gòu)分析,如關(guān)注邑內(nèi)支配者、被支配者等層面的秩序變動(dòng)。
縣制起源不僅是一個(gè)政區(qū)地理、行政區(qū)劃的歷史地理學(xué)問題,還是一個(gè)社會(huì)形態(tài)、政治結(jié)構(gòu)變動(dòng)下的官僚制起源與央地關(guān)系問題。既然討論“起源”,需要立足更大歷史背景,厘清分封制與郡縣制的關(guān)系,不僅上溯春秋,更遠(yuǎn)追周初分封的“王畿—諸侯”、諸侯“國—都—邑”政治秩序,關(guān)注“公邑—私邑”統(tǒng)治模式。既然討論“演變”,需要考慮不同時(shí)期與地域的邑、縣形態(tài)差異,建立適用前后時(shí)空、較為客觀且可供比較的基本參照,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轄域概念,可使線索梳理落至實(shí)處。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對秦漢縣制有經(jīng)典表述:
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xiāng)、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綏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fù)黃綬。
上述記載反映的實(shí)際是西漢中后期情況,不但與秦及漢初不同,而且應(yīng)是據(jù)不同時(shí)期史料綴集而成。從史實(shí)而言,秦縣長官只設(shè)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已依萬戶區(qū)分大、小縣,但“減萬戶”仍為令;秦代縣丞、尉秩五百石至三百石,西漢初年縣丞、尉秩五百石至二百石,而非“四百石至二百石”。從史料而言,因“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故“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當(dāng)在陽朔二年(前23年)之前;“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所據(jù)材料在綏和二年(前7年);文末兩次綬制變更的交代,又在建平二年(前5年)以后。
所謂“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皆秦制也”,指秦漢縣域受人、地兩種要素影響,而以前者為主導(dǎo),面積相對穩(wěn)定。“方百里”之“方”,有方圓、周圍(周長)、平方、正方形邊長、廣袤相加之和(周長之半)等多種意見。先秦至魏晉,“方百里”之“方”,既不指周長、廣袤之和,也不是正方形的邊長,而是絕長續(xù)短而成的正方形面積。“方百里”之“百里”,指邊長為100里,“方百里”為10000平方里。由此,相較于將“方”釋為“縱橫”、理解為正方形邊長,“方百里”之“方”、“百里”應(yīng)分作解釋。這種描述面積卻交代邊長的方式,頗具古代特色。
漢晉縣城、縣境統(tǒng)計(jì),分為兩種方式。縣城統(tǒng)計(jì)城圍周長,如青島土山屯漢簡《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稱,“城一舟(周)二里百廿五步”;或兼記城高,如時(shí)代靠后的郴州晉簡《桂陽郡計(jì)階簿》稱,“便城周匝一里十五步高一丈五尺”、“晉寧城周匝一里二百卌步高一丈五尺”,對后世多將“方某里”理解為周圍、周長,應(yīng)有影響。縣域主要計(jì)算東西、南北長度,如《堂邑元壽二年要具簿》稱“縣東西百卅五里五十步,南北九十一里八十步”,與尹灣漢簡《集簿》記西漢成帝時(shí)東海郡“界東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及《漢書·地理志》后序載“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格式全同,開啟后世地志州府縣境書寫傳統(tǒng)。《后漢書·東夷列傳》云東沃沮“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里”,記東西、南北長度而非面積,恰與“方百里”折算方形面積而側(cè)重交代邊長的體例近似。堂邑縣“戶二萬五千七”,屬萬戶以上大縣。縣境東西長135里50步,南北長91里80步,與“大率方百里”相合。
漢唐以“百里”作為縣、縣令的代稱。儒家希慕古制,崇尚周統(tǒng),“百里”修辭甫現(xiàn),便與先秦古制建立聯(lián)系。東漢明帝語作“郎官上應(yīng)列宿,出宰百里”,班固薦謝夷吾文稱“及其應(yīng)選作宰,惠敷百里”。此尚屬將漢制與春秋情形比附。順帝初,左雄上疏:“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李賢注“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理解略嫌保守。王莽復(fù)古改制,還曾付諸實(shí)踐:“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眾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眾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此本諸《禮記·王制》而稍有調(diào)整。先秦一“同”為“方百里”,新莽“公”級(jí)諸侯封地為“土方百里”,與縣“大率方百里”正相對應(yīng)。實(shí)將漢縣淵源上溯,與周初分封比附,建立起更久遠(yuǎn)的歷史聯(lián)系。
漢代視郡如邦國,郡守另稱“千里”。有意思的是,《漢書·百官公卿表上》雖言“縣大率方百里”,但未用“郡大率方千里”一類表述。前引尹灣漢簡《集簿》記東海郡東西、南北長度均在500里左右,可稱“大率方五百里”。當(dāng)然,漢郡不等同于秦郡,秦分天下為36郡,郡目后有添增,西漢成帝時(shí)已有103郡。秦及漢初每郡統(tǒng)縣在15—20個(gè),秦縣“大率方百里”,更為名副其實(shí)。秦已有“千里”之稱,睡虎地秦簡《語書》記“志千里使有籍書之,以為惡吏”,整理小組注作“志,記。千里,指郡的轄境”,譯文作“由郡官記錄在簿籍上向全郡通報(bào),作為惡吏”。《語書》“有”多讀作“又”,“使”或作名詞,上接“千里”,指行縣郡吏,此句可作“志千里使,有(又)籍書之,以為惡吏”。秦簡出土地安陸屬于秦南郡,取直線距離最長者,南郡東西長約1063里、南北長約613里,與“千里”呼應(yīng)。秦郡中大于南郡,特別是東西、南北皆超千里之郡,尚有一些,故秦郡可稱“千里”甚至“大率方千里”。
明晰秦漢郡縣實(shí)況,引入“方百里”、“千里”等轄域概念,可進(jìn)一步激活舊有史料,使對縣制起源的長時(shí)段考察獲得可供比較的基本參照。
二、西周分封與“公邑—私邑”復(fù)合制
武王伐紂,小邦周克大邑商,西周以宗周、成周為王畿之域,畿外廣行分封。王畿、諸侯的轄域關(guān)系,文獻(xiàn)多有載錄,《左傳》記“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shù)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yù)解一“圻”為“方千里”,一“同”為“方百里”。據(jù)此,天子王畿是諸侯(公侯)之地的100倍。西周王畿為關(guān)中盆地及洛陽地區(qū),西起寶雞,東至洛陽,東西約1058里,南北不及千里。
關(guān)于周初諸侯如楚、魯、齊、晉轄域,一些記載可資參考。《左傳》記“無亦監(jiān)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shù)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提到楚國在若敖、蚡冒、武王、文王時(shí)期,疆域不過一同,未及方百里。至春秋晚期,楚土已達(dá)數(shù)個(gè)方千里。《史記·楚世家》又記“熊繹當(dāng)周成王之時(shí),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并記楚武王熊通稱“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所涉“子男之田”、“子男田”為方50里或70里,與《左傳》“土不過同”相對應(yīng)。《孟子·告子下》提到魯、齊初封,云“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均為方百里。至戰(zhàn)國,齊境廣大,魯也“大啟爾宇”。“今魯方百里者五”,并非方五百里,而是指5個(gè)方百里,即疆土擴(kuò)大5倍。又《史記·晉世家》載,“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記叔虞封在河、汾以東,最初僅為方百里之地。
此外,司馬遷有概括性表述:“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武王、成、康所封數(shù)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wèi)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過或損”。可與“列國一同”、“諸侯一同”對照,反映當(dāng)時(shí)普遍情形。對此,呂思勉云,“蓋周初大國之封,僅等秦漢時(shí)之一縣,其后開拓,浸至倍蓰”;林沄也提到,春秋初晉國興起以前,今日霍縣以下長約200公里的汾水谷地中,至少有霍、趙、揚(yáng)、賈、郇、韓、耿七國,平均相距只有30公里,分布密度和漢代的縣大體相當(dāng),也和成湯之國大小略同。似乎可以把這種規(guī)模的國,看作商代至西周的通常格局”。西周所封一國,與秦漢一縣面積相當(dāng)。先秦的“國”往往指稱諸侯都城,即邦之都邑,反映諸侯始立時(shí)的規(guī)模形態(tài)。
西周分封,周室王畿不及“方千里”,仍可稱“千里”;所封魯、齊、晉、楚,初始轄域?yàn)?ldquo;方百里”。同時(shí),王畿有內(nèi)服王臣的采地、各諸侯朝覲周王的“朝宿邑”,加之遷入的被征服國的貴族以及士農(nóng)工商各有居地,“這些都使當(dāng)時(shí)的王畿好像一個(gè)‘大雜院’”。雖然如此,“從實(shí)際情況看,王畿地區(qū)幅員遼闊,除去各級(jí)貴族的領(lǐng)邑,其主體還是王室或王朝所有”。由上論之,周行分封延續(xù)較久,除周禮、周德之盛外,王畿轄域與一畿外諸侯的關(guān)系比理論上是100∶1,實(shí)際也是“方百里”諸侯的數(shù)十倍以上,而非僅僅數(shù)倍,從而建立起周室與諸侯相當(dāng)懸殊的力量對比。這一制度設(shè)計(jì)及實(shí)施,恐怕才是西周“天子—諸侯”秩序得以長久維持并有條件調(diào)整鞏固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礎(chǔ)上看,西周分封制向秦漢郡縣制的演變,不宜視作簡單線性發(fā)展。周室在王畿之外,固然選擇了較為徹底的分封制,但分封的先決條件是周室通過滅國并地,掌握諸多以都、邑為中心的土地。前引《史記·晉世家》記周公滅唐后,成王再封叔虞于唐,可見唐被誅滅之后,自然直屬周王。諸侯受封疆土,原本皆在周室之手,分封之前,可視作周王所掌畿外之公邑。至于王畿之內(nèi),由于未盡用作封賜,周王開展直接統(tǒng)治的都、邑自然更多,治理模式更趨穩(wěn)定,性質(zhì)屬于周王所掌畿內(nèi)之公邑。王畿內(nèi)外之公邑進(jìn)而對應(yīng)地方行政體制,設(shè)有職官系統(tǒng)。李峰提到:“在王邑地區(qū)也存在著大量由國家直接控制、獨(dú)立于宗族結(jié)構(gòu)之外的邑,而這些邑則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員進(jìn)行管理。”陳絜關(guān)注周代農(nóng)村基層聚落,認(rèn)為不但所涉城邑、鄙野有專人管理,而且“地方管理的行政化及層級(jí)化傾向顯然已經(jīng)存在”。由此而言,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應(yīng)是認(rèn)知縣制起源的關(guān)鍵。
如從名實(shí)之“實(shí)”著眼,后世君主委派官吏直管的縣,無論大小,都指國都之外、懸系于君主之地。嚴(yán)耕望注意到,早期文獻(xiàn)“縣”或作“寰”,“古者寰縣通用”;李家浩認(rèn)為,“‘縣’的出現(xiàn)至少可以追溯到西周。那時(shí)所謂的‘縣’系‘縣鄙’之‘縣’,指王畿以內(nèi)國都以外的地區(qū)或城邑四周的地區(qū)”。由于周初諸侯封地大小僅后世一縣之地,將縣的起源上溯西周,自應(yīng)從王畿而非諸侯內(nèi)部尋索。不過,縣如作邊鄙理解,則無公私之分,因此,應(yīng)當(dāng)聚焦周王直轄公邑,而非國都之鄙。進(jìn)而,西周是否使用“縣”稱,又是否假借“瞏”、“寰”以表示“縣”,反而并不重要。
縣制可溯至西周君主對公邑的直接統(tǒng)轄,兩周之際歷史變動(dòng)影響了這一進(jìn)程。一方面,西周滅亡,平王東遷,轄域驟減,力量頓衰;另一方面,繼承畿內(nèi)政治結(jié)構(gòu)并擴(kuò)展疆土的勢強(qiáng)諸侯,對縣制起源產(chǎn)生更直接的影響。輔助平王的晉、鄭二國發(fā)展,可為早期例證。《左傳》記載,“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此事《史記·晉世家》作“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hào)為桓叔”;《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曲沃大于國”,及“曲沃強(qiáng)于晉”,“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晉本為甸服之諸侯,今晉又封桓叔于曲沃,封邑(曲沃邑)大于“國”(晉都邑),違背“諸侯立家”之制,故稱“建國”。曲沃邑在封桓叔之前,自屬晉君直轄公邑。至于都邑、封邑的等級(jí)制度,見于《左傳》:“及(鄭)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yán)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國”之下大型聚邑稱“都”,“國”、“大都”、“中都”、“小都”分等不是據(jù)轄域面積,而是城的周長,城周(城墻總面積若干雉)比為9∶3∶1.8∶1。可以發(fā)現(xiàn),城周比差距小于王畿與初封諸侯的轄域比。相較天子、諸侯之爭,諸侯內(nèi)部更易引發(fā)權(quán)力紛爭。武姜為少子共叔段求取封邑,曾向長子鄭莊公先后請求過嚴(yán)、京二邑,兩者皆屬鄭君直轄公邑,前者因戰(zhàn)略地位重要被莊公婉拒。周室雖行分封,但天子王畿、諸侯封域?qū)嶋H都存在封賜私邑與君主直轄公邑兩種形態(tài),因此可稱為王權(quán)主導(dǎo)下的“公邑—私邑”復(fù)合制。
三、春秋楚縣及其“國”、“都”特征
西周分封下王畿、諸侯的統(tǒng)治形態(tài),經(jīng)歷東周初葉如晉、鄭等國發(fā)展后,在春秋時(shí)期呈現(xiàn)地域性特征,并發(fā)生進(jìn)一步演變,楚、晉、秦對縣制確立影響較大,下面依次探討三國縣制。
先看一般認(rèn)為縣制淵源所在的楚。《左傳》云:“初,楚武王克權(quán),使斗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quán)于那處,使閻敖尹之。”這一記載揭示兩種管理方式:其一,將新地改為公邑,派臣直接管理;其二,將新地民眾遷至已有公邑,由該公邑長官集中管理。權(quán)、那處皆在郢都之北,楚北邊防御的另外兩座重鎮(zhèn)是申、息。申、息同屬滅國立縣,由楚君直轄。二縣統(tǒng)地廣闊,供給軍賦且軍力強(qiáng)大,可對抗晉國南下攻蔡的“成師”,既與秦漢“大率方百里”的縣不同,又與西周“方百里”、一同之地的諸侯有別。《左傳》記載,“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楚君派巫臣治理申,供應(yīng)軍賦。“所以為邑也”,指公邑;“賞田”指析分出封賞之用的私邑,屬于別為之田、別為之邑。
楚圍鄭時(shí),鄭伯曾有“使改事君,夷于九縣”的辭令,杜預(yù)注曰“楚滅九國以為縣,愿得比之”,陸德明、孔穎達(dá)圍繞所滅九國為何,有不同解釋。楊慎、汪中等明清學(xué)人提示“九”為虛數(shù),猶言諸縣。然各家在“九縣”對應(yīng)楚所滅之國一點(diǎn)上,意見一致,不宜解作“鄭國土地較大,非僅楚之一縣,故云九縣”。至于“當(dāng)指未滅而服屬于楚者”、“國而曰縣,比之于楚內(nèi)臣也,謙辭”之說,也可斟酌。徐少華認(rèn)為,楚滅某國,往往不是將之亡國絕嗣,而是降為附庸、納為屬國,并安置他處。田成方認(rèn)為“楚滅國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是在形式上武力降服諸小國,不立即亡其國、絕其祀、編其民,但在其附近置‘縣’,縣公由楚王直接任命,實(shí)質(zhì)上占有其地、勞役其民”。因而,這些諸侯復(fù)國恢復(fù)舊制并不困難。“九縣”不意味著楚滅國后重新規(guī)劃出若干公邑,而表示楚滅掉大小不等的諸侯,將之直接轉(zhuǎn)為縣。此“縣”不代表“縣鄙”之縣,也不表示“縣邑”之縣。“夷于九縣”與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有所不同。晉國將兩家卿大夫的封地重新規(guī)劃,分設(shè)七縣與三縣;如按楚國處置,祁氏、羊舌氏被滅后,只能對應(yīng)“夷于二縣”。楚縣雖由楚王直轄,但對內(nèi)部形態(tài)觸動(dòng)不大,轄地變更不多。
楚之大縣,除申、息外,還有陳、蔡、東不羹、西不羹。據(jù)《左傳》,楚莊王十六年(前598),因夏徵舒之亂伐陳,首次“縣陳”,聽取申叔時(shí)勸諫后,令陳復(fù)國;楚靈王時(shí),楚公子棄疾圍陳,再次縣陳,由穿封戌擔(dān)任陳公;稍后,楚“滅蔡”,在陳、蔡、東西二不羹筑城,公子棄疾擔(dān)任蔡公。此事清華簡《系年》作“縣陳、蔡,殺蔡靈侯”、“既縣陳、蔡”(簡99、104)。公子棄疾滅蔡時(shí),陳公穿封戌已去世,陳、蔡一度由公子棄疾管理。《史記·楚世家》載叔向語作“君陳、蔡,方城外屬焉”,《陳杞世家》作“使棄疾為陳公”,《管蔡世家》作“使棄疾為蔡公”,側(cè)重稍異,含義實(shí)同。靈王深感得意,夸耀稱“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大臣又言“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將四縣稱作“四國”,與楚國并列。楚在陳、蔡、東不羹、西不羹筑城設(shè)縣,長官稱陳公、蔡公,或“陳、蔡公”,甚至“蔡侯”,實(shí)與申、息及“夷于九縣”近似,雖轄地廣大,但直接轉(zhuǎn)為楚君轄地,比附而稱“四國”。《左傳》載楚莊王讓申叔語,“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將“縣公”與“諸侯”并舉,當(dāng)因此故。楚稱王較早,縣尹稱公,與諸侯名號(hào)、地位相當(dāng)。
《左傳》《國語》及《史記》都提到陳、蔡、二不羹等“賦皆千乘”,以此可知楚縣規(guī)模。《漢書·刑法志》引先秦舊制云: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此說又見《周禮·地官司徒·小司徒》鄭玄注引《司馬法》及《晉書·地理志》總序引《司馬法》,文字略異。諸侯依可供兵車分作百乘、千乘、萬乘三個(gè)等級(jí)。“一同百里”,原對應(yīng)周初封侯的“方百里”,然東周諸侯大有擴(kuò)張,此時(shí)已對應(yīng)卿大夫的較大采邑。“千乘之國”并非“方千里”,而是“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指邊長316里的方形,面積為99856平方里,是“一同百里”的近10倍,此對應(yīng)當(dāng)時(shí)較大諸侯。“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恰與之對應(yīng),實(shí)際相當(dāng)于10個(gè)方百里的縣邑,故縣公可與諸侯并列。《左傳》載伍奢被殺后兩子之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杜預(yù)集解曰,“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伍尚作為棠邑大夫,稱“棠君”而非“棠公”,與晉縣相當(dāng)(詳見下節(jié))。
陳、蔡、二不羹不但被稱“四國”,而且特別呈現(xiàn)“是四國者”、“又加之以楚”的并列關(guān)系,初觀令人困惑,實(shí)與秦及漢初郡、內(nèi)史的關(guān)系相近。早期秦郡相當(dāng)一封國,故郡早期也稱邦。郡最初實(shí)際相當(dāng)于以內(nèi)史為中心橫向派生的軍事及行政管理區(qū)。楚國陳、蔡、東西不羹等大縣,規(guī)模接近秦郡;楚國縣公地位相當(dāng)于后世郡守。相關(guān)并列關(guān)系可示意為:
秦國:秦中(內(nèi)史)—郡
楚國:楚—四國
得志的楚靈王后來失意于乾溪,楚右尹子革貢獻(xiàn)三策:其一,“請待于郊,以聽國人”;其二,“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其三,“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郢城之外,楚王主要依靠“大都”。不過,“大都”與“國”的關(guān)系,多強(qiáng)調(diào)城周等級(jí),不能完全反映轄域、戶口及軍力對比;同時(shí),“大都”既可封賜,又可直轄,不足以體現(xiàn)與君主的領(lǐng)屬關(guān)系。楚縣又稱“國”、“都”,顯示對楚而言,滅國為縣并非革命性制度變化。
四、春秋晉縣“封邑”說、“雙重性質(zhì)”說辨疑
顧頡剛認(rèn)為晉縣與楚縣分屬兩個(gè)系統(tǒng),晉縣是卿大夫采地。增淵龍夫發(fā)現(xiàn)“以趙衰為‘原大夫’亦可叫‘原守’,也可記為‘以原封’”,認(rèn)為“春秋時(shí)代的晉縣同時(shí)兼具封邑和公邑兩種不可分的性格”。關(guān)于公邑、私邑主官稱謂,孔穎達(dá)雖云“公邑稱大夫,私邑則稱宰”,但黃以周、顧棟高、增淵龍夫利用相近論據(jù),考證二稱實(shí)際相通。既然公邑、私邑長官皆可稱大夫,那么根據(jù)史載“某(邑)大夫”,其實(shí)不足以判斷此為公邑還是私邑,晉縣性質(zhì)值得重新探討。
《左傳》記載:“晉侯作二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過去將此視作晉縣的較早記錄。《左傳》稱“賜”,《史記》一處稱“賜”、兩處稱“封”,指晉滅耿、魏二國,將之封賜給有功的趙夙、畢萬。二人成為晉國大夫,兩地成為二人私邑。《史記·魏世家》記載:“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后封,列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徙治安邑。”魏武子“襲魏氏之后封,列為大夫,治于魏”,既與“以魏封畢萬”呼應(yīng),又與“徙治霍”、“徙治安邑”并列。“徙治霍”、“徙治安邑”是私邑的轉(zhuǎn)移,安邑由此為魏氏核心城邑并成為后來魏都。《左傳》又記載:
與之陽樊、溫、原、  茅之田。晉于是始起南陽……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茅之田。晉于是始起南陽……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晉侯問原守于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平定王子帶之亂,得到封賜,趙衰、狐溱分任原、溫兩邑大夫。此前,晉文公咨詢“原守”人選,勃鞮認(rèn)為趙衰在流亡時(shí)忠君忘我、患難與共、最可信任,“故使處原”。“原守”指代晉君治理原邑,“處原”而不稱“封”、“賜”可為證。《韓非子·外儲(chǔ)說左下》記載相近,唯人名、情節(jié)稍有出入:“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太平御覽》三次引《韓非子》相關(guān)內(nèi)容,一般認(rèn)為“此即趙衰事也”。
可以看到,與“原守”、“故使處原”對應(yīng)處,《韓非子》及《太平御覽》引作“乃舉以為原令”、“乃舉為原令”、“以為原令”、“而使為原之守”,任命及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受戰(zhàn)國晚期職官表述影響,三處“原令”指原縣之令,“原守”指代替君主管理公邑。《史記·魏世家》提到魏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nèi)稱治”,《韓非子·外儲(chǔ)說左下》云,“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守鄴”與“原守”、“原之守”相近,“鄴令”與“原令”對應(yīng)。至于“以原封”的記載,其實(shí)不見于《左傳》,而出現(xiàn)于《史記·晉世家》:
(晉文公)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于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首句至“魏犫為右”一段,參引《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紀(jì)事;“冬十二月”以下,為《史記》獨(dú)有。值得注意的是,《冊府元龜》在“封邑”條下列舉“趙衰,晉大夫。晉文公伐曹、衛(wèi),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而非“趙衰為原大夫”的前一則。至于《史記·趙世家》所載“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未言是晉文公元年(前636)事;《史記·晉世家》所載“命趙衰為卿”,《左傳》作“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左傳》又云“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御狄。趙衰為卿”,任卿已至?xí)x文公八年。
綜上可見,晉文公元年,趙衰因流亡時(shí)的忠君表現(xiàn),被選任為“原守”,代晉君守原邑,后世習(xí)稱“原令”;至?xí)x文公四年,晉伐曹、衛(wèi),趙衰以兵先下山東,因功又被封于原,原邑始為趙衰封邑。《左傳》這則關(guān)鍵史料不能說明春秋晉邑具有雙重屬性,反映的實(shí)是公邑、私邑間的轉(zhuǎn)移變動(dòng)。
《左傳》所載晉國先茅之地的變動(dòng),也不足以說明晉縣的雙重性質(zhì)。魯僖公三十三年“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預(yù)集解曰:“先茅絕后,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晉先將該地賜予先茅為食邑,先茅無后,收回此地。現(xiàn)因胥臣推薦郤缺之功,晉重新賜于胥臣。先茅之地的變化為:公邑(晉)→私邑(先茅)→公邑(晉)→私邑(胥臣)。《左傳》又記:“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州縣作為晉君直轄公邑,早年賜給欒豹;欒氏滅亡后,又復(fù)歸晉君,范、趙、韓三家都很覬覦。趙文子(趙武)揭舉理由是:“溫,吾縣也。”杜預(yù)集解曰:“州本屬溫。溫,趙氏邑。”州邑原屬溫邑之一部,而溫邑屬于趙氏,“吾縣也”,指溫是趙氏的直轄私邑。范氏、韓氏反對的理由是,晉君曾將州賜于大夫郤稱,州由此與溫分離,至今已傳三家。晉君將直轄公邑析分(賜予)不限于州邑,因此不能追溯原初情形而要求所有權(quán)。趙文子為正卿主政后,推辭稱自己尚不能治理好已有私邑,怎能又貪圖州邑。“溫,吾縣也”、“余不能治余縣”的表述,史料并不多見。這是寬泛的變通性表述,強(qiáng)調(diào)的是由卿大夫直轄但未被進(jìn)一步向下分賜的私邑,不宜理解過實(shí)。晉縣與公邑的差別并不明顯,它們與卿大夫私邑都不涉及對原有氏族秩序的破壞重組。
再來看晉縣設(shè)職及運(yùn)作,這在《左傳》中有所記載:
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fù)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一句,杜預(yù)集解為“屬趙武”,孔穎達(dá)正義曰,“諸是守邑之長……此言問其縣大夫,問絳縣之大夫也。絳非趙武私邑,而云則其屬者,蓋諸是公邑,國卿分掌之,而此邑屬趙武也”,后人多從之。其實(shí),確認(rèn)絳縣老人年齡、身分及籍貫,固可問詢本人,從行政程序而言,仍應(yīng)聯(lián)系屬縣長官,以行政方式予以確認(rèn)。同時(shí),趙國公邑明確,數(shù)目有限,絳縣近在國都區(qū)域,趙孟任晉國正卿,主持國事,不太可能連絳縣大夫都不認(rèn)識(shí),而要通過聯(lián)系編戶的方式確定。此應(yīng)指趙武召問絳縣大夫,確認(rèn)老人是否屬于絳縣。隨后,趙武向老人致歉并任以為縣師,將輿尉撤職,不僅反映晉卿與晉縣的關(guān)系,而且表明晉縣已置縣大夫、縣師、輿尉。輿尉征發(fā)縣中“輿人”,從事筑城在內(nèi)的縣內(nèi)外徭役,與秦漢縣尉征發(fā)縣內(nèi)男子服役已較相近。
晉縣轄域規(guī)模及內(nèi)部形態(tài),可參《左傳》下述記載:
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強(qiáng)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余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bào)其大恥。
魯昭公五年(前537),晉楚聯(lián)姻,晉臣韓起、叔向送晉宗女至楚,楚王有意施刑二人以羞辱晉國,后被薳啟強(qiáng)勸阻。韓起代表晉國六卿,對應(yīng)上卿一級(jí);叔向代表晉國大夫,對應(yīng)上大夫一級(jí)。所列六卿和九位大夫,是晉國政治勢力的代表。參據(jù)杜預(yù)集解,韓襄即韓無忌,是韓起之兄;箕襄、邢帶是韓起同族;韓須是韓起嫡子,叔禽、叔椒、子羽三人是其庶子。“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指上述韓氏七人每人掌有一邑(韓須所對應(yīng)者,應(yīng)即韓起之邑)。每邑相當(dāng)于一大縣,以出軍賦,杜預(yù)集解稱“成縣,賦百乘也”。下云“羊舌四族,皆強(qiáng)家也”,杜預(yù)集解曰:“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此稱“四族”而非四人,其中叔向一族可與叔向子楊石對應(yīng)。韓、羊舌二氏所擁軍力,體現(xiàn)在“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一句。“十家九縣”之“十家”,杜預(yù)、俞樾理解不同,但“九縣”向無爭議。“九縣”之“縣”,指私邑規(guī)模相當(dāng)于標(biāo)準(zhǔn)縣者有九。其中,羊舌氏雖有強(qiáng)家四支,但“成縣”規(guī)模的大邑只有兩個(gè)。二氏所擁九邑比附九個(gè)“成縣”,可出兵車900乘。其余比附“成縣”規(guī)模者有40個(gè),可出戰(zhàn)車4000乘。清人黃以周云:“《周書·作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為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法也。”晉縣規(guī)模雖小,但較為整齊統(tǒng)一。晉國“成縣”對應(yīng)方百里,與秦漢縣基本一致;而每縣出戰(zhàn)車百乘,與楚國陳、蔡“賦皆千乘”在出賦規(guī)格上相同,反映周土地舊制及經(jīng)濟(jì)形態(tài)仍然存續(xù)。
至春秋末葉,晉縣大夫選任及行政管理更為制度化,《左傳》記載:
(魯昭公二十八年)秋,晉韓宣子卒,魏獻(xiàn)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涂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余子之不失職,能守業(yè)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后見于魏子,以賢舉也。
晉悼公后,六卿勢力漸強(qiáng),執(zhí)政先后經(jīng)歷趙武、韓起,又轉(zhuǎn)至魏舒(魏獻(xiàn)子)。《史記·韓世家》稱韓宣子(韓起)“與趙、魏共分”,而非“為國政”,與其他記載并不矛盾。顧頡剛認(rèn)為:“魏獻(xiàn)子當(dāng)國,他冊命一班縣大夫,其意義等于武王時(shí)的封國,表示出十足的封建色彩。”所論受《左傳》下文“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影響,但針對內(nèi)舉不避親,不代表魏舒任命晉縣大夫有分封性質(zhì)、封建色彩。“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是魏獻(xiàn)子以晉國執(zhí)政身分作出決策,代表的是晉君。“祁氏之田”、“羊舌氏之田”,概指二氏擁有大小不等的眾多私邑。“以為七縣”、“以為三縣”,指由私邑再次轉(zhuǎn)為晉君直轄公邑;稱“七”、“三”,反映晉縣轄土已有穩(wěn)定標(biāo)準(zhǔn),所任晉縣大夫十人,就是公邑大夫。
晉縣長官選任根據(jù)功績、賢能,“皆受縣而后見于魏子”,及“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辛來!……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與后世縣級(jí)主官出宰百里前,面見君主或宰相,當(dāng)面聆聽訓(xùn)勉相近;“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與秦漢地方奏讞中央近似;魏戊作為魏氏一系,阻止大姓豪強(qiáng)賄賂魏獻(xiàn)子,以防地方司法受到干預(yù),與后世縣令長嚴(yán)守權(quán)責(zé)相近。不過,晉縣長官仍稱“大夫”,縣內(nèi)仍行周田舊制,仍有待進(jìn)一步演化,縣制的最終突破要看韓、趙、魏三國以及受三晉影響的秦國。
五、商鞅置令與秦縣官僚組織的建立
秦縣材料主要來自《史記》,而非《左傳》。秦人是很早臣服于周的一支外服邦伯勢力,周宣王時(shí)任秦仲為大夫,至莊公“為西垂大夫”,居于西犬丘。“為西垂大夫”,是以西犬丘作為私邑的周室大夫。至秦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正義》引韓安國之說:“秦穆公都地方三百里,并國十四,辟地千里。”此事較早記載見于《韓非子·十過》,王叔岷考辨“諸書皆言‘十二’,竊疑作‘十二’近塙”。《韓非子·有度》還提到,“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所載類似,恐非隨意表述。“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中,“開地”里數(shù)大體為“益國”數(shù)的十倍,所并之國,相當(dāng)于后世一縣之地。“開地”若干千里,對應(yīng)被并之國直線排列的長度。穆公時(shí),秦國以方300里擴(kuò)展,大體增加12(或14)個(gè)方百里,可折算為縱深千里。當(dāng)時(shí),秦在原約9萬平方里外,增加約12萬平方里,而非增加3倍以上規(guī)模。
商鞅變法前的秦縣,見于《史記》之《秦本紀(jì)》及《六國年表》:
(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秦獻(xiàn)公二年)城櫟陽……(六年)初縣蒲、藍(lán)田、善明氏……(十一年)縣櫟陽。
前者在春秋早期,后者在戰(zhàn)國中期,相距達(dá)300多年。兩者表述一致,均作“初縣”,反映秦人后來的整體認(rèn)知。“縣鄙”之“縣”,概言國都之外的周邊區(qū)域,春秋時(shí)武公“居平陽封宮”,在今陜西寶雞附近,邽、冀戎距平陽較遠(yuǎn),文獻(xiàn)也少見通過縣鄙延伸來擴(kuò)展疆土的記載。獻(xiàn)公二年(前383),“城櫟陽”;九年之后,“縣櫟陽”。所言“城某地”指構(gòu)建軍塞,反映軍事特征,西北漢簡多見“城官”,城官不治民,主要是軍塞性質(zhì)。與“城某地”相對,“縣某地”指設(shè)置地方行政機(jī)構(gòu),體現(xiàn)民政功能。秦之“初縣”,指首次以該地為秦君直轄公邑,并設(shè)置相應(yīng)行政管理人員及組織。
商鞅變法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是推行縣制,《史記》之《秦本紀(jì)》《六國年表》《商君列傳》均有涉及:
十二年,作為咸陽,筑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xiāng)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十二年)初(取)[聚]小邑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十三年)初為縣,有秩史。(十四年)初為賦。
居三年,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nèi)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xiāng)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quán)衡丈尺。
從縣制起源及諸國縣制比較的視野出發(fā),上述史料記載可作五點(diǎn)闡說。一是撰作特征。以秦遷都咸陽為界,商鞅變法一般被分作前后兩次,《秦本紀(jì)》記第一次變法,僅有“衛(wèi)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nèi)務(wù)耕稼,外勸戰(zhàn)死之賞罰……卒用鞅法……其事在《商君》語中”一句;但對第二次變法內(nèi)容,多有論及。《六國年表》載事簡略,未言第一次變法,僅記軍事、外交活動(dòng);對第二次變法遷都咸陽一事未提及,但對縣制推行、縣吏設(shè)置及土地、賦稅制度卻有交代。至《商君列傳》,兩次變法始同時(shí)說明。由此,《史記》涉及變法內(nèi)容,縣制出現(xiàn)次數(shù)最多,《史記》本紀(jì)、年表的重要性多高于列傳,可知商鞅變法諸舉措中,縣制推行實(shí)際頗為時(shí)人所重。
二是設(shè)縣背景。商鞅推行“農(nóng)戰(zhàn)”政策,構(gòu)建“君—民”聯(lián)結(jié),借此全面削弱貴族,為推行縣制提供基本前提。商鞅縣制實(shí)質(zhì)又是公邑、私邑之間的博弈,“縣—封邑”復(fù)合制與單一縣制不同,阻力、難度不可同日而語。某種意義上說,真正的困難恐怕正是全面推行縣制,因其動(dòng)搖宗室貴戚既有政治與經(jīng)濟(jì)基礎(chǔ)之故。商鞅首次完成這一變革,在諸雄中實(shí)現(xiàn)突破,意義不限秦國,難怪《史記》多次交代。
三是設(shè)縣方式。商鞅第二次變法,首先營建新都,“筑冀闕”、“作為筑冀闕宮庭于咸陽”、“大筑冀闕,營如魯衛(wèi)矣”,直追東方諸侯,代表秦建成等級(jí)規(guī)格相埒的新都。接著,由中央而地方,商鞅開始行政制度改革。秦既有聚邑一般規(guī)模較小,新營都邑后,地方公邑同樣參照東方,通過“并”、“集”、“聚”的方式,規(guī)劃升級(jí)為大縣。戰(zhàn)國城邑發(fā)展的趨勢是“萬家之邑”、“萬家之縣”。《戰(zhàn)國策》載趙奢語:“且古者,四海之內(nèi),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眾,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商鞅因應(yīng)這一形勢,“集為大縣”。秦大縣、小縣選擇以萬戶為界,萬戶以上大縣恰與“萬家之邑”、“萬家之縣”對應(yīng)。
四是縣令與官僚組織。商鞅縣制更重要的是縣令之置,從起點(diǎn)而言,戰(zhàn)國秦漢的縣由縣令到令、長,存在逐步發(fā)展的過程。從終點(diǎn)而言,又是東周秦縣主官由大夫到令的重大變化。后者地位、等次變化似乎不大,保持在大夫一級(jí),但縣大夫、縣宰具有貴族身分,縣令是領(lǐng)取固定俸祿的官吏,“令”本身凸顯對君命的貫徹。汲黯“其先有寵于古之衛(wèi)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shí)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后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汲黯家族自東周以來“世卿世祿”,長期擔(dān)任卿大夫,加之衛(wèi)國存古制較多,更保留不少舊時(shí)觀念。史料所記反映汲黯不愿為地方官的事實(shí),但先秦大夫往往代君理邑,外任公邑大夫,向不為恥。今汲黯恥被除任滎陽這一要縣之令,卻不惜“病歸田里”,從側(cè)面提示縣令、縣大夫的差異。
此外,秦職官稱謂存在上級(jí)參照下級(jí)的現(xiàn)象,部分稱謂呈現(xiàn)自下而上的延伸,為后世少見。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僑(矯)丞令’可(何)殹(也)?為有秩偽寫其印為大嗇夫”,以“有秩(嗇夫)”與“大嗇夫”對稱。“大嗇夫”主要指秦縣令,裘錫圭認(rèn)為:“‘嗇’是‘穡’的初文,‘嗇夫’的本來意思就是收獲莊稼的人。‘嗇夫’作為官名,首先應(yīng)該應(yīng)用于鄉(xiāng)嗇夫一類下級(jí)基層治民官吏。地位較高的治民官吏或其他官吏也稱為嗇夫的現(xiàn)象,只有在鄉(xiāng)嗇夫一類名稱使用了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shí)期以后,才有可能出現(xiàn)。”相比于郡,縣“俯親民事”,參照使用“鄉(xiāng)嗇夫一類下級(jí)基層治民官吏”才使用的稱謂。睡虎地秦簡《南郡守騰文書》記“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郡也用“嗇夫”來稱縣、道主官。
秦縣令稱縣嗇夫、大嗇夫,反映縣主官不僅成為貫徹君令的官僚,而且縣令設(shè)置初始,往往強(qiáng)調(diào)廣泛親近民事的服務(wù)屬性。“縣嗇夫”的用法,兩漢不復(fù)出現(xiàn)。西漢初,嗇夫稱謂仍存,但縣令、長已不稱嗇夫。漢承秦制,一些細(xì)微精神卻有變化。進(jìn)入東漢,縣主官被比附為縣宰、大夫,反而更為常見,體現(xiàn)先秦傳統(tǒng)的回潮。
秦縣設(shè)令晚于三晉,卻是在全面推行縣制下的統(tǒng)一舉措,有鑒于此前公邑、私邑長期并存,商鞅縣制是徹底的公邑化,最初并未給封賜私邑留下空間。這在公邑不落于權(quán)卿操控、公邑比重占據(jù)優(yōu)勢等方面,實(shí)現(xiàn)了革命性突破,是君主集權(quán)的真正加強(qiáng),由此顯得意義突出。《商君列傳》提到縣“置令、丞”,還顯示縣令之外的縣佐官也由中央任命。《六國年表》又記推行縣制的次年“初為縣,有秩史”,“縣有”之間不宜點(diǎn)斷,當(dāng)作“初為縣有秩史(吏)”。縣少吏包括有秩、斗食、佐史三級(jí),“有秩吏”是縣內(nèi)秩級(jí)最高的屬吏,作為縣下屬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人,由倉、司空、少內(nèi)等諸官嗇夫構(gòu)成,持小官印,須上級(jí)二千石官任命。有秩吏的普遍設(shè)置,反映秦縣廷在地方掌握較多資源,進(jìn)而具有較強(qiáng)控制力。同時(shí),秦及漢初往往縣、都官并稱,都官是中央諸卿、內(nèi)史、諸郡的下轄機(jī)構(gòu),與縣平級(jí)。參考現(xiàn)代行政學(xué),縣制確立初期的央地關(guān)系,主要呈現(xiàn)“條塊結(jié)合”特征。綜上來看,縣制核心是縣令設(shè)置與縣級(jí)官僚組織的基本建立。
五是縣制與田制。戰(zhàn)國時(shí)期,魏率先崛起,與文侯任用李悝變法發(fā)展生產(chǎn)多有關(guān)系。《漢書·食貨志上》記載:“是時(shí),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地方百里”對應(yīng)一縣之地,“提封九萬頃”、“為田六百萬畝”都是以周制百步為畝作為基準(zhǔn)。商鞅由魏入秦,變法涉及“為田開阡陌封疆”,與魏氏改行200步為畝不同。《史記·秦始皇本紀(jì)》文末附別本《秦記》,作“昭襄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學(xué)界過去對田制改革時(shí)間存在爭論,青川木牘載錄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為田律”,“更修”之“修”,不是修訂而是修復(fù)之意,“更修”指“重新公布過去制定的舊律文”,故田制改革仍應(yīng)系于商鞅。參《秦本紀(jì)》《六國年表》,田制頒行時(shí)間在普遍設(shè)縣之后,縣制確立是實(shí)施土地制度改革的基礎(chǔ)。這再次提示,縣制起源固然與社會(huì)組織的重大變動(dòng)有關(guān)、與經(jīng)濟(jì)制度的重新構(gòu)建相聯(lián)系,但核心是官僚組織的建立及運(yùn)行。
結(jié)語
本文引入“方百里”的縣域空間概念、“公邑—私邑”的統(tǒng)治模式作為兩條分析線索,為縣制起源研究提供新視角,重新探討中國古代政治體制的衍生過程。經(jīng)過分析,春秋之縣與戰(zhàn)國之縣,在性質(zhì)上具有一致性及密切聯(lián)系,而縣制更早的源流,即在西周時(shí)期周王與諸侯直接管理的“公邑”。在此基礎(chǔ)上,本文重新辨析《左傳》等先秦史料所見春秋縣制的基本特征,進(jìn)一步明確這一時(shí)期縣的性質(zhì),相較于中國學(xué)界所主張春秋晉縣為“私邑”、日本學(xué)界所主張春秋晉縣兼具公私雙重特征的看法,提出新認(rèn)識(shí)。本文提煉一條縣制起源發(fā)展的新線索,縣制起源時(shí)間也大為提前。
縣制起源背后,實(shí)際涉及對分封制、郡縣制的基本認(rèn)識(shí)。先秦秦漢由分封制到郡縣制的重要轉(zhuǎn)變,不宜視作簡單的線性發(fā)展,兩種制度也不宜截然兩分。中國古代行政體制具有很強(qiáng)的包容性和靈活性,分封制可以蘊(yùn)含郡縣制因素,郡縣制也可以采取一些分封制內(nèi)容。中國早期國家注重將血緣關(guān)系作為主要政治紐帶,以家族、宗族為統(tǒng)治基礎(chǔ)與依憑,過去強(qiáng)調(diào)分封制的徹底貫徹,但西周分封并不排斥君主對公邑的直轄管理,天子王畿、諸侯封域內(nèi),實(shí)際都存在封賜私邑(采邑)與君主直轄公邑兩種形態(tài)。“天子—諸侯”政治秩序得以確立,“諸侯”一端以及諸侯內(nèi)部層層分賜的基礎(chǔ)和前提,是天子及諸侯對直轄公邑的有效掌控。天子封建諸侯之后,秩序得以長久維持,也與天子仍然擁有較多直轄公邑、王畿對初封諸侯轄域形成優(yōu)勢力量對比,有重要關(guān)系。
這又進(jìn)一步反映,過去對“天子—諸侯”政治秩序中“天子”一端、對早期王權(quán)有所低估。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呈現(xiàn)內(nèi)聚型特征,君主集權(quán)理念始終貫徹其中,進(jìn)而在分封制下,以君主為核心的中央集權(quán)同樣較為突出,可稱“早期中央集權(quán)”。“在西周一朝的多數(shù)時(shí)期,王權(quán)都是王朝政治的主導(dǎo)力量”,“西周政治的主流仍是‘王權(quán)政治’,‘世族政治’只是短時(shí)期內(nèi)出現(xiàn)的‘非常態(tài)’現(xiàn)象”,可見,分封制背后的,完整圖景是王權(quán)主導(dǎo)下的“公邑—私邑”復(fù)合制。與之相應(yīng),郡縣制并不完全排斥分封,后世根據(jù)實(shí)際情況,又可在郡縣制主導(dǎo)下實(shí)行多元化綜合治理。
由分封制、郡縣制的分析,進(jìn)而可涉及對周秦變革的認(rèn)識(shí)。柳宗元《封建論》云:“彼封建者……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封建非圣人意也,勢也。”王夫之云:“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而為天下計(jì),(利)[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古人肯定由封建到郡縣的歷史突破與進(jìn)步,同時(shí)也提示,背后實(shí)須有相應(yīng)變化的動(dòng)力與條件。中國古代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跨越,君權(quán)固然是國家形態(tài)變革的主導(dǎo)力量,但又非唯一要素,官僚制特別是行政制度的發(fā)展確立,為相關(guān)變革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分封制與郡縣制的關(guān)聯(lián)比較,實(shí)際揭示出君主制、官僚制兩個(gè)而非一個(gè)面相。探討君主制,不宜脫離君主之下的官僚制;分析官僚制,更不宜忽略君主的在場。君主制、官僚制二者如何結(jié)合,又如何不斷實(shí)現(xiàn)整體性演化,仍將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研究的恒久論題。
(作者孫聞博,系中國人民大學(xué)國學(xué)院、“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fā)展工程”協(xié)同攻關(guān)創(chuàng)新平臺(tái)教授;來源:《歷史研究》2024年第1期)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gè)人觀點(diǎn),不代表本站觀點(diǎn),僅供大家學(xué)習(xí)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wǎng)站,如涉及版權(quán)和名譽(yù)問題,請及時(shí)與本站聯(lián)系,我們將及時(shí)做相應(yīng)處理;
3、歡迎各位網(wǎng)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wǎng),依法守規(guī),IP可查。
作者 相關(guān)信息
內(nèi)容 相關(guān)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wù) 新前景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qū)建設(shè) ?

? 黨要管黨 從嚴(yán)治黨 ?

 侯立虹:也談“無官不貪”與“無官不想貪”
侯立虹:也談“無官不貪”與“無官不想貪” 3年落馬14人!光大原董事長李曉鵬落馬背后,“河南幫”浮出水面
3年落馬14人!光大原董事長李曉鵬落馬背后,“河南幫”浮出水面
 宋珊珊:數(shù)字技術(shù)賦能 提升幸福指數(shù)
宋珊珊:數(shù)字技術(shù)賦能 提升幸福指數(shù) 泥腿看客:納瓦爾尼之死,除了警惕“顏色革命”,還要警惕“遠(yuǎn)程投毒”
泥腿看客:納瓦爾尼之死,除了警惕“顏色革命”,還要警惕“遠(yuǎn)程投毒” 丁堡駿:必須改變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教學(xué)和學(xué)科建設(shè)的現(xiàn)行體制和格局
丁堡駿:必須改變西方經(jīng)濟(jì)學(xué)教學(xué)和學(xué)科建設(shè)的現(xiàn)行體制和格局? 社會(huì)調(diào)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