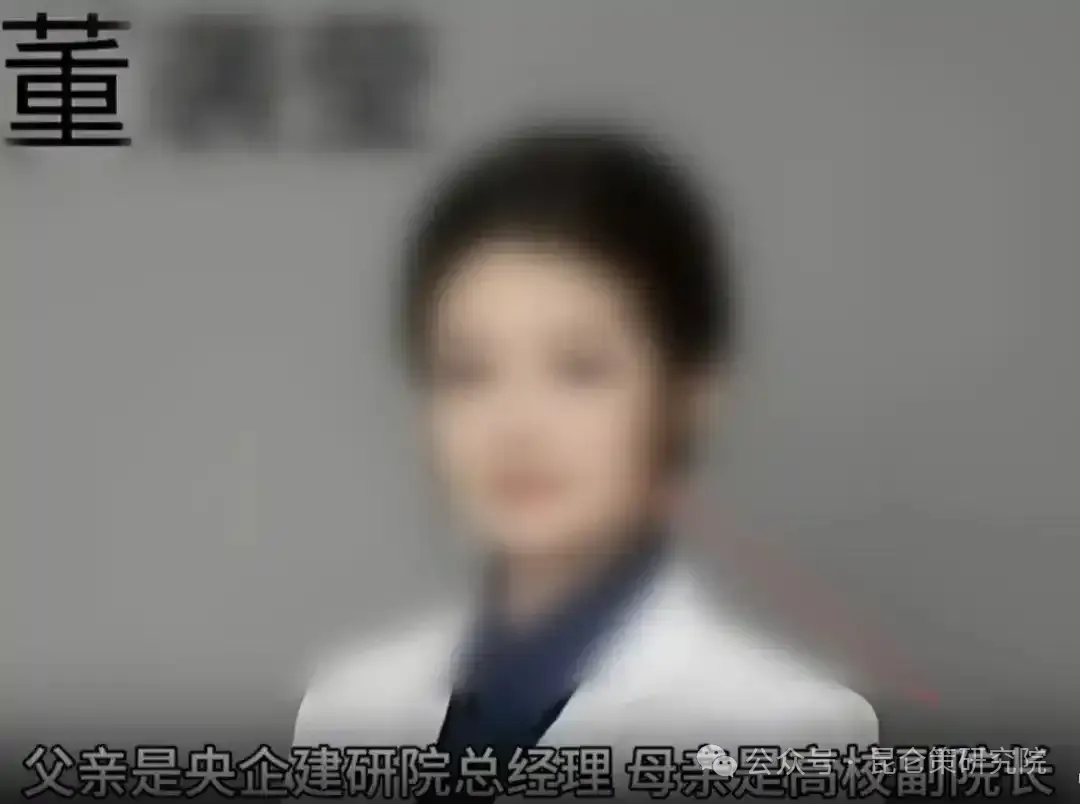作者王學忠是一位下崗工人。30年來,下崗工人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經歷著命運跌宕的痛苦,品味著生活困頓的苦澀,積蓄著日益深重的哀怨,燃燒著富兒們不能體會的希望。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下崗工人都能將自己的人生體驗發而為歌。從這種意義上說,學忠是幸運的,“文章憎命達”的“幸”,“國家不幸詩家幸”的“幸”,以群體痛苦為巨大代價的“幸”。
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創新農村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建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直接關系到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關系農村基本經濟經營制度的發展方向和農村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也關系到國家的戰略全局。近年來,上海始終堅持維護好、實現好、發展好農民利益,注重頂層設計,創新改革形式,完善政策措施,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有序進行,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鄧小平(1992.7)
元旦過后整理書桌,發現幾份深埋數月的美國《高等教育記事》雜志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的副刊(The Chronicle Review),有點過時,但還是翻閱一遍。與正刊不同,副刊的文章大多出自教授之筆,不長也不術語連篇,話題相對活潑;當然,是否每個作者都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則另當別論。
比如,2014年2月28日那一期,登了一篇題為“非批判性思維在中國”的文章 (“Non-Critical Thinking in China”)。作者,美國某高校一位英語系副教授。
有兩種“確權”,一是對集體建設用地和宅基地的確權,要求全國在2013年底完成(現在不知道完成了沒有,因為后來沒有了下文);另一種是對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民承包經營權的確權,現在正在全國試點。對這兩種確權,被吹得神乎其神,說是“第二次土改”。長期以來,筆者對此百思不得其解,有如下質疑:
今天在中國出現了兩條明顯的道路,一條路線是我們究竟是站在大多數人一邊、國家利益的一邊,還是站在少數人一邊,這是個重大的問題。
今天我講一個很前沿的問題,就是今天進城的農民工還回不回得去農村。農民工回不回得去農村要從兩個層面去講,第一個層面是農民工能不能在城市安居,這個問題很重要,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工業化發展能不能讓進城的農民工體面的住下來。第二層是假使農民工在城市住不下來,那他回農村能不能生活下去。這個問題也很重要,回不回的來的問題究竟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都需要仔細認真談論。
一、引言 恩格斯曾經指出,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是現代全部社會體系所依以旋轉的軸心。自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資本和勞動之間的矛盾一直是社會最基本的矛盾,勞動關系一直是社會經濟生活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在當代中國,勞動關系同樣是整個社會最基本的經濟關系。構建和諧勞動關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國策建言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